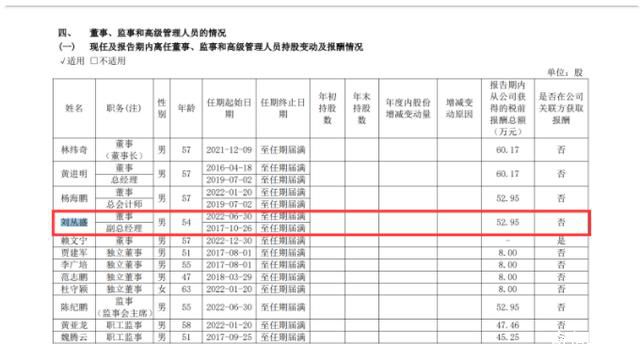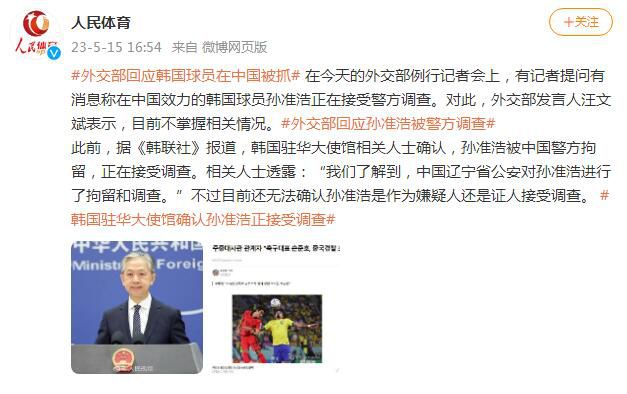調查顯示8成年輕人有生育意愿 面對生娃他們在猶豫和擔心什么
導讀:因為步入青春期后擁有了弟弟妹妹,提前體驗了做母親的艱辛;因為見證了媽媽對于家庭的退讓與犧牲,重新思考自己理想的婚育模式……這些經歷
因為步入青春期后擁有了弟弟妹妹,提前體驗了做“母親”的艱辛;因為見證了媽媽對于家庭的退讓與犧牲,重新思考自己理想的婚育模式……這些經歷,讓李顏、汪逸欣、黃啟政等8位浙江工業大學的“00后”大學生開始思考,是什么讓當下的一些年輕人在婚育面前裹足不前?

在過去一年半時間里,他們組成調查團隊,走進浙江各地社區、幼兒園、婦幼醫院,發放千余份問卷,訪談80位不同年齡段的婚育主體,其中超過7成問卷和訪談聚焦“00后”。他們試圖探索青年婚育低欲化背后的成因,也是在調研過程中,這個小團體的成員們,重新打量自己對婚育的理解。他們的調查結果或許不能覆蓋“00后”這個龐大的群體,但這種聲音也足以讓我們思考。
近八成有生育意愿
22歲的李顏和21歲的汪逸欣,全程直擊過母親照顧幼兒的艱辛,也曾深度參與其中。
2016年,也是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的第一年,李顏的媽媽取下了留在肚子里十多年的節育環。不久之后,這個義烏姑娘多了一個小15歲的弟弟。
不同于李顏的“被通知”,衢州姑娘汪逸欣則擁有“投票權”。那是一個尋常的放學后的夜晚,父母突然召開家庭會議,鄭重地問16歲的汪逸欣,要不要留下這個孩子。
“留。”那一刻,汪逸欣只感到興奮,她天然覺得這世上將從此多一個,可以無條件去愛、去信任的親人,是一種神奇的體驗。
生育,是刻在每代人基因里的本能。但在不同時代背景下,政府對人口政策不同,導致各年齡層會形成不同的婚育觀。從建國之初的“多子多福”,到此后推崇“少生優生”,現如今出臺更積極的鼓勵生育政策背景下,網絡上一些年輕人卻推崇“不婚不育保平安”。
但浙工大團隊的調查結果顯示,事實并非如此。針對18歲至35歲的中青年,調研小組收集回1466份有效調查問卷,結果顯示,近8成的人有生育意愿,而最主要的原因是“喜歡孩子”。
李顏和汪逸欣都對擁有自己的孩子有憧憬,源于有弟弟妹妹的經歷。因為弟弟,李顏又看到年近50歲的父親露出乖巧、憨厚的笑容,柔聲細語地問,“這個好不好?”家庭群填滿關于弟弟的討論,“學習累了,看一眼群里,就被他的可愛治愈了。”
李顏害怕青蛙,但每當弟弟抓來蝌蚪和跳跳魚想嚇她一跳,她只覺得快樂。
汪逸欣則享受每個早上妹妹撲到自己身上喊她起床的時刻,“如果我說要睡個懶覺,她會乖乖地把我的窗簾拉上、再小心地關上門。”妹妹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常令汪逸欣驚喜,“長大后,我的知覺好像變得遲鈍。我似乎是從10到100在不停地往前走,但從0到10的那個過程我已經忘記了。但她會帶我重新恢復那種感受。”
但與此同時,她們也體會到作為母親的種種艱辛和不易。這些無法完全被母愛的光輝掩蓋。
從泡奶粉、喂奶、拍奶嗝開始,汪逸欣陪伴著這個妹妹長大。自高中起,她的寒暑假都圍著妹妹轉,“小時候,給她換尿布、換尿不濕、洗屁股、洗澡、哄睡;長大一點,就陪她出去玩、上興趣班。”汪逸欣最害怕妹妹哭鬧,“她一哭起來,我就覺得難受。”
同樣全程參與撫養弟弟的李顏,也有相似的痛苦體驗。有一次,母親半夜起床,發現弟弟發了高燒。李顏陪著母親把弟弟送去醫院,兩人忙到凌晨4點,幾乎一夜未睡。
汪逸欣認識到,“做姐姐和做媽媽的心態還是不一樣的。”一旦成為母親,自己就要為孩子承擔全部的責任,“只有我覺得能夠給他(她)提供足夠美好的世界時,我才會把他(她)帶到這個世界上。”
時常缺席的父親
楊怡然是這個項目的發起人,2001年出生于安徽。她長著一張清秀的臉,但仔細看,左臉頰上留著一道陳年的疤。那是讀幼兒園時,被調皮的男孩抓傷的。而她被欺負的原因是,“沒有爸爸”。
小學三年級前,她跟隨母親在安徽生活,父親在杭州工作。邊工作邊獨自帶娃,母親的時間總是不夠用。楊怡然對兒時忙碌的清晨記憶深刻——很慌亂,得同時做幾件事,比如,一邊吃飯、一邊整理衣物。然后,母女倆一路奔跑到公交站,她獨自坐上四十分鐘的公交去學校。
母親很少向楊怡然抱怨辛苦,但有一天,她在房間里突然暈倒,“后來,我才知道她是太累了。”
這8位“00后”大學生,大都對“喪偶式育兒”不陌生。“我家就是典型的‘喪偶式育兒’。”李顏感嘆。
弟弟出生后,母親與日俱增的白發和越來越差的身體狀況令李顏心酸。“一開始,她兼顧著工作,孩子半夜總醒,一天只能睡兩三小時,第二天照常上班,壓力很大。”
李顏回憶說,母親熬了兩年后,無奈地選擇休假全職帶娃,可她開始失眠,白發長得特別多。48歲的母親打算再過兩年就提前退休,全心撫育弟弟。
她的父母是同家公司的工程師,但父親選擇了外派項目。小時候,父親常年在國外,母親也工作繁忙,四年級起,李顏開始寄宿生活,“我一周回家一次,我爸一年才回家一兩次。”弟弟出生后,父親回國,但依舊常年在外地,回家的頻率變成一兩個月一次。
在弟弟的成長過程中,李顏雖然感受到父親也逐步為家庭妥協,但母親的職業發展和人生節奏,似乎更是理所當然地被生育打斷。
23歲的黃啟政是團隊中唯一的男生。父母原本是金華同家單位的公務員,黃啟政出生后,母親辭職全心帶娃,偶爾做些零工。直到黃啟政讀初中,母親正式回歸職場,但她再也回不到過去的崗位,只能做起銷售。
小時候,黃啟政只覺得母親煩,天天圍著自己轉;長大后,他對母親愈發同情。在他的記憶里,父親對母親總是很苛責。“他希望家里的一切井井有條,比如冰箱里,醬料、蔬菜、水果等有各自固定的位置,但我媽不是那種會細致地物歸原位的人。他每次回家,打開冰箱,看見物品沒有整整齊齊擺放,就要責怪我媽。”黃啟政說,因為冰箱這件小事,父母吵過無數次架。
“你為什么不能去收拾呢?”黃啟政不解地質問父親。父親會一次次強調賺錢養家的他有多么辛苦,“在他眼里,我媽的工作可有可無,有大把的空閑時間去收拾好家。”
后來,在參與婚育意愿調查的過程中,黃啟政為父親的行為找到了更明確的定義——“詐尸式育兒”。
當他們走進杭州多個社區調研,見到了更多的全職媽媽,而在家庭教育中,青壯年男性普遍缺席。同時,家庭中的男女雙方對從事無薪家務工作的認知存在較大差異——多數女性表示自己承擔了更多的育兒工作,但多數男性認為是平等分擔的。
這些“00后”認為,在一個家庭中,父親的作用同樣不可或缺,甚至足以塑造下一代的婚育觀。
汪逸欣讀小學前,父親也在外地工作,幾個月見一次,“后來,他回家發現我都不認識他了,他就換了工作,回到衢州。”
妹妹出生后,汪逸欣發現父親自覺地承擔起更多的育兒責任——接送幼兒園、哄睡、陪玩、做家務……她覺得,正是父親的舉動,讓家庭走向理想的模樣。
“如果你未來的伴侶像你爸這樣,主動承擔育兒責任,會不會減輕你對婚育的憂慮呢?”面對這個問題,汪逸欣格外堅決和果斷,“沒有如果,他一定要這樣才可以。”李顏也笑著補充說,如果沒有這樣的男性伴侶,那就“先不生,再等等,等他們醒一醒。”
“可靠的育兒伴侶”
很長一段時間,黃啟政覺得父親“好自私”。
他讀高二時,父母矛盾重重,可母親最終為了家庭退讓。黃啟政清楚母親的選擇是為了他,可這種察覺又讓他感到沉重,“那種犧牲太大了,是我沒辦法想象的。”
“母子終究是兩個完全獨立的個體,在我身上投入這么多,值得嗎?萬一我沒有辦法長成你想象的那樣,最后,你會不會很失望?”黃啟政把自己的疑惑拋給母親。母親只輕描淡寫地回答他,“你是我兒子,每個母親都是這樣的。”這并未消解黃啟政的困惑,他時常為母親感到遺憾,“她本可以過上更好的人生。”
黃啟政把父母的婚姻描述為“最平凡的模式”——相親結識、互為初戀,因為門當戶對,走向婚育,經歷中年危機后,互相妥協,回歸平淡……
可在這個“00后”男孩眼中,這也是他最不想要的婚姻模式。
“不想要‘差不多’就進入婚姻;我也沒辦法做到,為了一個終有一天要走向分離的孩子,傾注那么多精力、時間和金錢,甚至為了他影響自己的人生選擇。”
對黃啟政而言,婚育是一件純粹、神圣又需要慎重的人生選項。一些女性朋友的觀點,也與他不謀而合。“我們不抗拒婚育,但它不是人生的必選項。”李顏和汪逸欣一致認為,婚育的前提是擁有一個能夠承擔育兒責任的可靠伴侶。
對待婚戀,青年人越來越不愿意將就了。調研小組向18歲至35歲的中青年發放出1466份問卷,其中,近8成的人堅持“繼續等待,找到理想的人再結婚生子。”
22歲的溫州姑娘葉非凡對孩子有更明晰的憧憬,“我覺得人在衣食無憂之后,最大的敵人是孤獨感。”當幾位同齡人都對婚育表達猶疑時,她坦言,自己挺想要一個孩子,“在我衰老之后,想看到身邊有一個年輕的延續。”
她有一個交往了一年多的男朋友,兩人都喜歡孩子。某一天,當男朋友提到自己8歲弟弟的可愛,隨口說出“我要是能生我弟,我什么都不怕。”葉非凡卻警覺數學系的男朋友完全無法感知生育帶來的痛苦,“如果他不能理解我在生育上的犧牲和付出,我是堅決不會想要生孩子的。”
后來,葉非凡不斷向男朋友灌輸自己了解到的婚育風險,試圖讓他理解生育造成的女性困境。
自大二起,團隊中的這幾位“00后”都選修過女性主義相關的課程,比如,《媒介與性別文化》、《女性文化與現代文學》,等等。“這些課給我們的啟發和收獲很大,男生更應該聽一聽。”葉非凡覺得,這些文科生的選修課應該變成更多人的必修課。
重新思考“人生的選項”
婚育世界的海洋,“水溫”似乎遠超他們的想象。
出于好奇,李顏很早就在網上看過女性生產過程的3D模擬視頻,“看得挺痛苦。”汪逸欣則在網上看到不少關于生育對身體傷害的研究,“有項研究說,生育會使細胞加速衰老11年,真的嚇到我了。”
在對未來的想象中,楊怡然曾想當然地認為會生育兩個孩子,“一兒一女,湊個好字。”這個想法的萌生要追溯到小學,她和朋友們玩“壓手腕”的游戲——打掌心握手腕,手腕鼓出幾個“包”就預示未來生幾個小孩。楊怡然的手腕上總會出現兩個“包”,她隱隱把它當作人生的預兆,也在無形中順從了父母口中關于完美家庭的描繪。
可如今,當她和朋友們完成這組調查,楊怡然對婚育的想法悄然改變,“也許我只會生一個孩子。”面對這道“孕”算題,她開始考慮能否找到可以分擔育兒責任的伴侶、以及能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實現“精養”。
養育成本大幅提升,投入與產出不成正比,成為不少年輕人進入婚姻與生育的第一道門檻。在這些“00后”的調研中,有近九成的青年將“經濟與居住條件”視為影響婚育的第一大要素,其次則是養育成本、工作壓力、身體狀況。
樂高、計算機、感統訓練、體能課、信息課……汪逸欣總帶著4歲的妹妹上五花八門的課外班,為此,父母一年投入幾萬元。教育觀念迭代更新,妹妹的同學家長都是“90后”,這對“70后”父母顯得有點脫節,可也不得不迎合當下的教育風向。
“在這個成功論的社會,競爭風氣濃郁,父母都不想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如果無法帶孩子逃離這種評價體系,就只能不斷地付出、投入、雞娃。”汪逸欣不想讓孩子進入這樣“內卷”的世界,經歷她曾走過的不快樂的旅程,“只有我具備足夠的經濟基礎,才能讓孩子擁有自由選擇的底氣。”
李顏的母親同樣不希望她重蹈覆轍。前不久,當父親問李顏,“大學畢業后,想不想去我們單位工作?”一向溫和的母親卻大發雷霆,“你胡說什么?她要是到我們單位上班,在我們單位找對象,以后過得又跟我一樣苦。”那一天,李顏難得地捕捉到母親的一絲反抗,但依舊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孩子。
對于生育帶來的不平等,當上代人選擇默默隱忍時,這群“00后”卻通過自己的調研,用一種新的方式思考,為他們的未來規劃出不同的婚育路線。
-
 攀枝花公園豹子胖成了“豹警官” 年紀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2024-03-07 21:07:32近日,四川攀枝花公園內一只圓潤的金錢豹走紅,網友調侃稱胖成了豹警官,引發關注。園方回應:年紀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近日,攀枝
攀枝花公園豹子胖成了“豹警官” 年紀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2024-03-07 21:07:32近日,四川攀枝花公園內一只圓潤的金錢豹走紅,網友調侃稱胖成了豹警官,引發關注。園方回應:年紀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近日,攀枝 -
 多家金店足金報價突破650元每克 黃金的價格又漲了2024-03-07 21:05:30近日,國際金價連續上漲,黃金飾品價格也一漲再漲。截至7日上午,多家品牌金店的價格足金價格已經突破了650元 克。一覺醒來,黃金的價格又
多家金店足金報價突破650元每克 黃金的價格又漲了2024-03-07 21:05:30近日,國際金價連續上漲,黃金飾品價格也一漲再漲。截至7日上午,多家品牌金店的價格足金價格已經突破了650元 克。一覺醒來,黃金的價格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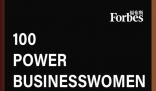 2024福布斯中國杰出商界女性 周群飛喻麗麗上榜2024-03-07 21:03:13今日,福布斯中國發布2024杰出商界女性100榜單,這是福布斯中國第10次發布該榜單,通過這份榜單可以看到中國商業世界的女性群像。其中,上
2024福布斯中國杰出商界女性 周群飛喻麗麗上榜2024-03-07 21:03:13今日,福布斯中國發布2024杰出商界女性100榜單,這是福布斯中國第10次發布該榜單,通過這份榜單可以看到中國商業世界的女性群像。其中,上 -
 呼倫貝爾現“寒夜燈柱”現象 場面奇幻而震撼2024-03-07 20:59:026日凌晨,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夜空中出現寒夜燈柱現象。夜色中一束束光柱直沖蒼穹,場面奇幻而震撼。雖已過驚蟄,但位于中國北疆的內蒙古呼
呼倫貝爾現“寒夜燈柱”現象 場面奇幻而震撼2024-03-07 20:59:026日凌晨,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夜空中出現寒夜燈柱現象。夜色中一束束光柱直沖蒼穹,場面奇幻而震撼。雖已過驚蟄,但位于中國北疆的內蒙古呼 -
 蔡瀾上海餐廳菜品有異物被罰5萬 有顧客在菜品中吃出異物2024-03-07 20:55:49近日,蔡瀾上海餐廳因生產經營混有異物的食品,被上海市黃浦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5萬元,引發關注。據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站近日消息,
蔡瀾上海餐廳菜品有異物被罰5萬 有顧客在菜品中吃出異物2024-03-07 20:55:49近日,蔡瀾上海餐廳因生產經營混有異物的食品,被上海市黃浦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5萬元,引發關注。據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站近日消息, -
 兩男子起沖突被各自妻子緊緊抱住 家有賢妻禍事少2024-03-07 20:54:056日,有網友發視頻稱,北京兩男子街頭起沖突,雙方妻子死死抱住制止。目擊者表示:其中一位妻子被丈夫抱摔草里兩次都沒松手。家有賢妻禍事
兩男子起沖突被各自妻子緊緊抱住 家有賢妻禍事少2024-03-07 20:54:056日,有網友發視頻稱,北京兩男子街頭起沖突,雙方妻子死死抱住制止。目擊者表示:其中一位妻子被丈夫抱摔草里兩次都沒松手。家有賢妻禍事 -
 北京未開放個人申領三代社保卡 后續將逐步啟動2024-03-07 20:51:52近期,有群眾咨詢如何領取第三代社保卡,對此,3月7日,北京市人社局發出溫馨提示,當前,本市第三代社保卡換發工作正在分批次進展中。自今
北京未開放個人申領三代社保卡 后續將逐步啟動2024-03-07 20:51:52近期,有群眾咨詢如何領取第三代社保卡,對此,3月7日,北京市人社局發出溫馨提示,當前,本市第三代社保卡換發工作正在分批次進展中。自今 -

-
 女性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2024-03-07 20:46:45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月經不調可能會引發嚴重疾病嗎?知名專家在線互動解決你的問題。月經是女性生殖健康晴雨
女性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2024-03-07 20:46:45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月經不調可能會引發嚴重疾病嗎?知名專家在線互動解決你的問題。月經是女性生殖健康晴雨 -
 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生5.5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2024-03-07 20:42:04據中國地震臺網正式測定,3月7日18時6分在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生5 5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緯33 58度,東經93 01度。震中5公里
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生5.5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2024-03-07 20:42:04據中國地震臺網正式測定,3月7日18時6分在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生5 5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緯33 58度,東經93 01度。震中5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