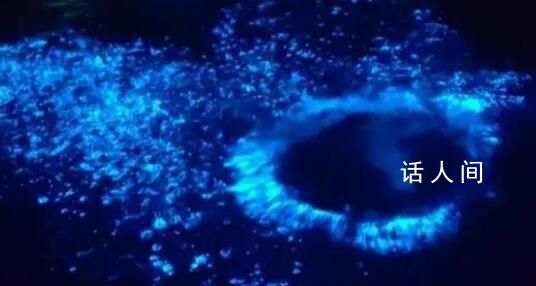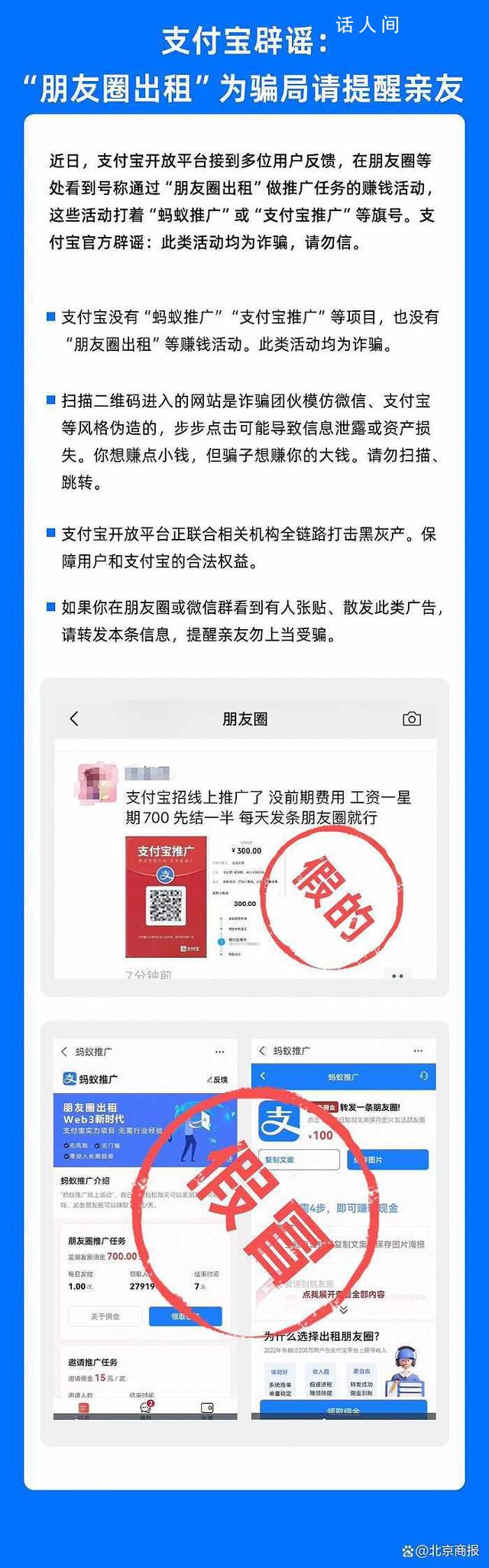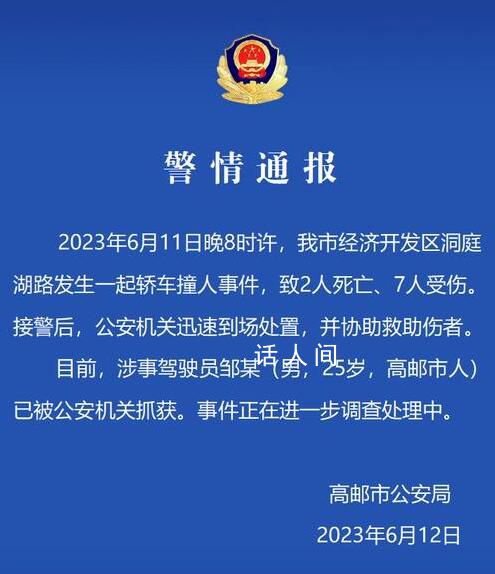朋友圈三天可見是不合群表現?不合群的人有哪些表現
導讀:近日,朋友圈三天可見的設置引發熱議。它也可以避免我們的過去被翻出,也可能會讓我們失去與過去的聯系,甚至會讓人感到孤獨。三年前,我應
近日,“朋友圈三天可見”的設置引發熱議。它也可以避免我們的過去被翻出,也可能會讓我們失去與過去的聯系,甚至會讓人感到孤獨。

三年前,我應聘一份互聯網的工作,進入到第三輪面試時,面試官向我提出了一個令我措手不及的問題:“你為什么從來不發朋友圈?”驚訝之下,我停頓了幾秒,憑借本能快速給出了一個最樸實的回答:“我不是從來不發,只是最近三天沒發,我的朋友圈設置成了三天可見。”對方聽畢,沒有就這個問題繼續糾纏,而是徑直跳轉到了下一個問題。雖然最終我還是得到了那份工作,但直到現在也不知道這個答案是否令對方滿意。從那以后,我總是不斷回想,不愛發朋友圈是個問題嗎?難道這代表了一個人不合群?
自從朋友圈開發出“三天可見”的功能,我便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感覺收獲了一項類似隱身術的超能力。在那以前,我總是頭一天情感充沛地發完朋友圈,第二天便心懷羞恥地將其刪掉,刪完又覺得生活的記憶也隨之消失,不免為此感到遺憾。很多時候,記憶總是需要依附一些記錄才能得以保留,不是嗎?但“三天可見”解決了這個問題。
“三天可見”還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是避免被“挖墳”。隨著微信好友的數量急劇膨脹,我們已經很難再用“好友”關系來界定通訊錄里的人。到目前為止,我的微信通訊錄里有2049個人,其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我已經想不起是誰,還有三分之一的人跟我僅有一兩次的對話記錄。如果這2000多號人都能翻到我十年前的朋友圈,總讓我有種站在明處被暗處之人圍觀的不安感。畢竟,如今誰的通訊錄里不是充滿了錯綜復雜的關系?親人、同事、朋友、合作對象以及各種無法歸類的人,他們原本應該待在各自的平行宇宙里互不牽連,被安放在MSN、QQ、釘釘以及電話簿等不同分類的區域里,但朋友圈的“大雜燴”打破了這種平衡。
事實上,在那場面試結束后的三年里,我在朋友圈里的活動開始全面收縮。不僅設置了三天可見,也越來越少更新狀態,更新頻率從以周為單位,逐漸變成以月為單位。以前經常會發一些個人生活的碎片,比如去過的餐廳、參加的聚會、游玩的照片,現在基本只發一些與公共領域有關的話題,比如看過的文章、對逝者的悼念。在朋友圈里與友人的互動也越來越少,盡量秉持“能點贊就不評論,能略過就不點贊”的原則,最大限度地減少能量的消耗。
相信除了我,越來越無法掌控朋友圈關系的大有人在。一位朋友告訴我,他的微信通訊錄里已經達到3000余人,他每刷一次朋友圈,就會順手刪掉幾個人,因為很多人他已經想不起來是誰,還有一些因為時過境遷已經疏于聯系,留著聯系方式也無用。他對朋友圈的印象甚至比我更糟糕,甚至不惜動用“Low”這個形容詞。他將自己朋友圈里的人大致分為兩類:一類以曬優越感為主,包括喝了什么名酒、買了什么好車、交了什么新朋友,處處展示高人一等的姿態;另一類是以刷存在感為主,喜歡在朋友圈高談闊論,無論看見什么都要下場評論兩句,生怕錯過“在場”的憑據。長此以往,他便將自己不喜歡的行為反觀為鏡,每當自己想要發什么動態,腦子里便回蕩起一個聲音:“不要成為自己討厭的人。”最后索性作罷,收起手機。
這位朋友的心態,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解讀為逃離社交網絡的“自證陷阱”。當朋友圈里涌進越來越復雜的關系,社交平臺便成為一個自我展演的舞臺,展演的動作也開始隨之變形,人人都想竭力扮演討喜的角色。這樣的陷阱并不獨屬于社交網絡,而不過是現實生活的延伸。美國社會學家歐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早在上世紀50年代便洞察到這一社會心理,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中,他建構出“戲劇論”用以探討日常生活中人與人之間的互動秩序,將人們的日常活動比作劇場上的演出。戈夫曼發現,當個體出現在他人面前時,總是按照一種籌劃好的方式來行動,以一種既定的方式來表現,以期控制他人所接受的情景印象,也就是所謂的“印象管理”,并通過區分前臺和后臺來區隔展演的舞臺和真實的世界。
復雜的社交網絡無疑放大了人們展演的欲望。無論是精挑細選的圖片,抑或是苦思冥想的文案,無一不是對“理想自我”的塑造,成為一種苦心籌謀的交際策略,這就導致真實的自我被刻意隱藏甚至遭到抑制,不切實際的幻象成為最高標準。而從中衍生出的比較心理,又將所有人拖下無法窮盡的漩渦,在焦慮和疲憊的狀態中循環往復。美國心理學家簡·M.騰格(Jean M.Twenge)和W.基斯·坎貝爾(W. Keith Campbell)將這種過度自我欣賞的頑疾命名為“自戀流行病”,因其把每個人都變成了只愛自己倒影的納喀索斯,他們同時認為“網絡2.0時代”就是病灶所在,在社交網站的助力下,自戀現象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蔓延至一場“全球性的瘟疫”。
朋友圈成為令人越來越有負重感的存在,并不是因人性格決定的,背后實在是有一些人類天性的共通點。英國人類學家、進化心理學家羅賓·鄧巴(Robin Dunbar)曾提出過“150定律”,該定律指出,人類智力或資源允許一人擁有穩定社交關系的人數是150個左右。這意味著,雖然人類文明程度越來越高,但人類的社交能力與石器時代沒什么兩樣。朋友圈這種超出極限的負荷,在一場熱鬧喧囂過后,最終還是會讓人感到疲于應付,從關系和信息過載的場域中離開。
眼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進行“社交齋戒”,試圖以各種斷舍離的方式奪回自主權。豆瓣上此起彼伏地出現各種“不發朋友圈”或“戒斷社交媒體”的小組,B站、抖音、小紅書等泛娛樂平臺的興起,也為逃離社交網絡的人提供了不同選擇的陣地。由Quest Mobile在2019年發布的《在校大學生洞察報告》顯示,年輕人的微信人均使用時長相較2018年下降了6.3%。由凱度發布的《2018年中國社交媒體影響報告》顯示,社交媒體對用戶產生消極影響的比例,從2017年的89%上升至93%。
伴隨著社交網絡無孔不入地蔓延,它帶來的消極影響正大范圍侵蝕個體的心靈。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曾用“群體性孤獨”來形容信息技術時代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當人過多地依賴信息技術與人進行交流時,人與人之間的真實連接反而變弱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它讓人形成幾種錯覺:一、我們可以把精力分配到任何我們想關注的地方;二、總會有人傾聽我們;三、我們永遠都不用獨自一人。特克爾認為,社交媒體加深了“我分享,故我在”的思維定勢,讓人通過不斷地分享行為來確認自身的存在感,聯系別人僅僅是為了減少焦慮,這既不會加深我們與對方的連接,也難以讓自己從孤獨中解脫。
德國哲學家韓炳哲也曾在《透明社會》一書中對信息時代否定一切距離的氛圍敲響警鐘,他認為這樣一種“透明社會”無益于人類心靈的棲居,因為人類靈魂需要另一種空間:“在那里沒有他者的目光,它可以自在存在。它身上有一種不可穿透性。完全的照明會灼傷它,引起某種精神上的倦態。”
自從開啟社交降級后,我感到自己終于從眾多無意義的社交活動中解放出來,輕松地解除了被復雜欲望越捆越深的枷鎖。外出旅行或是跟朋友聚會時,我不再花更多時間專門拍照,而是靜心享受所到之處的美景美食,專注于跟身邊人相處的點點滴滴。我也不再焦慮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或分量,而是精心打理每一段獨處的時光,真摯且實在地擁抱生活。或許,這已經開始接近奧地利作家彼得·漢德克(Peter Handke)所提倡的“親近世界的倦怠”:隨著自我逐漸弱化,自我存在的重心從自我轉移到世界。現在,我也可以像漢德克那樣悠悠地說出:“倦怠是我的朋友。我重新回歸到世界之中。”
如果再讓我重新回答一次三年前面試官的問題,我想對他說:“活在朋友圈的人,未免太累了。”
-
 龍行龘龘 為何生僻字熱起來了?2024-02-06 18:05:07中國農歷龍年將至,龘字一躍火出了圈,成為生僻字界的扛把子,引起民眾關注和好奇。為何生僻字又熱起來了?從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24年春節聯
龍行龘龘 為何生僻字熱起來了?2024-02-06 18:05:07中國農歷龍年將至,龘字一躍火出了圈,成為生僻字界的扛把子,引起民眾關注和好奇。為何生僻字又熱起來了?從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24年春節聯 -
 被困高速3天3夜 小伙稱像人在囧途2024-02-06 17:57:352月6日消息,據國內多家媒體報道,從杭州駕車回重慶老家的駱先生,滯留高速公路3天3夜后,終于駛入暢通路段,跟家人團聚。駱先生表示:就像
被困高速3天3夜 小伙稱像人在囧途2024-02-06 17:57:352月6日消息,據國內多家媒體報道,從杭州駕車回重慶老家的駱先生,滯留高速公路3天3夜后,終于駛入暢通路段,跟家人團聚。駱先生表示:就像 -
 新郎接親被新娘親友堵樓下要中華煙 目擊者:新郎最終無奈答應2024-02-06 17:54:482月5日,江蘇淮安新郎接親遇女方親友鬧喜,被堵要求發30條中華煙,目擊者:新郎最終無奈答應。結婚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事關一生的大事,但是
新郎接親被新娘親友堵樓下要中華煙 目擊者:新郎最終無奈答應2024-02-06 17:54:482月5日,江蘇淮安新郎接親遇女方親友鬧喜,被堵要求發30條中華煙,目擊者:新郎最終無奈答應。結婚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事關一生的大事,但是 -
 外國醫生回應在武漢機場跪地救人 機場可用的儀器設備和積極的響應令人印象深刻2024-02-06 17:53:035日,武漢天河機場一老人突發心臟病,一外國醫生伸出援手急救。外國醫生回應:機場可用的儀器設備和積極的響應令人印象深刻。2月5日中午12
外國醫生回應在武漢機場跪地救人 機場可用的儀器設備和積極的響應令人印象深刻2024-02-06 17:53:035日,武漢天河機場一老人突發心臟病,一外國醫生伸出援手急救。外國醫生回應:機場可用的儀器設備和積極的響應令人印象深刻。2月5日中午12 -
 湖北新郎用8臺四驅拖拉機迎親 對你的愛就像拖拉機爬坡轟轟烈烈2024-02-06 17:43:05近日,道路結冰導致普通車輛難以通行,湖北一新郎用8臺拖拉機當婚車車隊迎娶新娘。網友評論:對你的愛就像拖拉機爬坡,轟轟烈烈。農村道路
湖北新郎用8臺四驅拖拉機迎親 對你的愛就像拖拉機爬坡轟轟烈烈2024-02-06 17:43:05近日,道路結冰導致普通車輛難以通行,湖北一新郎用8臺拖拉機當婚車車隊迎娶新娘。網友評論:對你的愛就像拖拉機爬坡,轟轟烈烈。農村道路 -
 霍建華李凱馨親密合照 感謝林心如的熱情招待2024-02-06 17:33:19霍建華全面開啟內地營業,目前和李凱馨主演新劇《他為什么依然單身》殺青,李凱馨曬出和霍建華以及林心如夫婦的合影,單獨和霍建華的合影引
霍建華李凱馨親密合照 感謝林心如的熱情招待2024-02-06 17:33:19霍建華全面開啟內地營業,目前和李凱馨主演新劇《他為什么依然單身》殺青,李凱馨曬出和霍建華以及林心如夫婦的合影,單獨和霍建華的合影引 -
 路面結冰小哥帶哈士奇送外賣 網友:這只狗的狗糧都是自己賺來的2024-02-06 17:31:172月3日,湖北地區遭遇大雪天氣,路面結冰,給人們的出行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位外賣小哥想出了一個獨特的辦法,他帶著一只
路面結冰小哥帶哈士奇送外賣 網友:這只狗的狗糧都是自己賺來的2024-02-06 17:31:172月3日,湖北地區遭遇大雪天氣,路面結冰,給人們的出行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位外賣小哥想出了一個獨特的辦法,他帶著一只 -
 光大證券:A股市場機會大于風險2024-02-06 17:29:42光大證券研報表示,從估值、股債性價比、換手率、融資交易占比等指標來看,當前A股市場或已處于底部位置,疊加當前政策積極發力,以股票型E
光大證券:A股市場機會大于風險2024-02-06 17:29:42光大證券研報表示,從估值、股債性價比、換手率、融資交易占比等指標來看,當前A股市場或已處于底部位置,疊加當前政策積極發力,以股票型E -
 直擊湖北高速:有人因暴雪滯留2024-02-06 17:28:24昨晚到今天,湖北全境出現了降雪天氣,部分地區出現大到暴雪。積雪深度可達10厘米以上,局部15厘米以上。此輪低溫雨雪冰凍天氣過程,將持續
直擊湖北高速:有人因暴雪滯留2024-02-06 17:28:24昨晚到今天,湖北全境出現了降雪天氣,部分地區出現大到暴雪。積雪深度可達10厘米以上,局部15厘米以上。此輪低溫雨雪冰凍天氣過程,將持續 -
 武漢暴雪兩只孔雀被凍在墻頂 已成功救下孔雀狀態良好2024-02-06 16:48:002月4日,武漢園一工人人員清除積雪時發現兩只孔雀被凍在墻頂,景區工作人員回應:已成功救下,孔雀狀態良好。2月4日,武漢園博園一工作人員
武漢暴雪兩只孔雀被凍在墻頂 已成功救下孔雀狀態良好2024-02-06 16:48:002月4日,武漢園一工人人員清除積雪時發現兩只孔雀被凍在墻頂,景區工作人員回應:已成功救下,孔雀狀態良好。2月4日,武漢園博園一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