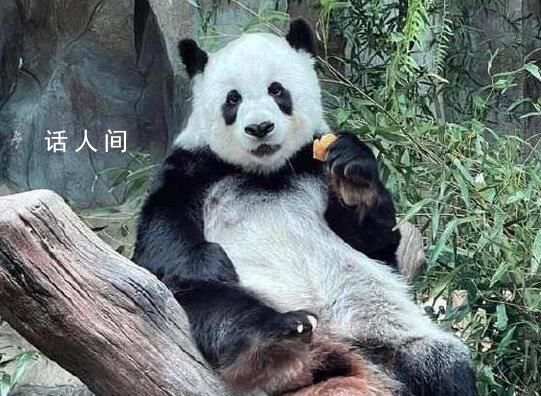大熊貓全球圈養數量達728只 從104只到728只破解大熊貓繁育三大難題
導讀:從全身粉紅不足100克的脆弱小生命,到重達百公斤深受世界人們喜愛的黑白精靈。從1990年的104只,再到如今的728只。每一只大熊貓健康茁壯成
從全身粉紅不足100克的脆弱小生命,到重達百公斤深受世界人們喜愛的黑白精靈。從1990年的104只,再到如今的728只。每一只大熊貓健康茁壯成長、大熊貓種群可持續發展、圈養大熊貓平均親緣關系值逐步降低、遺傳多樣性不斷上升的背后,是一代代“熊貓人”的“理想照進現實”。

1月25日,據國家林草局發布數據,我國大熊貓野外種群總量已從上世紀80年代的約1100只增長到近1900只,圈養種群逐步擴大,2023年全年繁育成活46只,全球圈養大熊貓數量達728只。
大熊貓“花花”
從104只到728只
破解大熊貓繁育“三大難題”
20世紀60年代,中國在有大熊貓分布的四川、陜西、甘肅建立了首批大熊貓自然保護區,開啟了我國大熊貓棲息地保護的征程。為摸清野外大熊貓“家底”,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我國啟動了大約每10年一次的全國大熊貓野外調查,了解了大熊貓種群數量、棲息面積、生活情況等信息。
為什么大熊貓幼崽那么小?為什么有很多早產兒?如何讓大熊貓順利產崽并成功存活?在長期開展大熊貓繁育研究過程中,工作人員發現,大熊貓配種后存在胚胎延遲著床的現象,它會選擇適宜的時機啟動胚胎發育,并在很短的時間讓寶寶出生,平均僅約17天。這項研究也首次從影像學上直觀地證實了大熊貓初生幼崽出奇弱小的原因,是大熊貓繁育研究工作中的一項重要成果。
“我國加強大熊貓遺傳學研究與管理,實施科學優化配對繁殖,將推動圈養種群擴大與完善種群結構、提高遺傳質量有機結合,有效維護了圈養種群的不斷擴大和遺傳結構的日益優化。”國家林草局野生動植物保護司二級巡視員張月介紹,在本世紀初,我國研究人員突破了大熊貓發情難、配種受孕難和育幼存活難等三大難題,大熊貓圈養種群逐步擴大。
此外,大熊貓圈養種群的平均親緣關系值也逐步降低,遺傳多樣性不斷上升。經科學評估,現有大熊貓圈養種群保持90%遺傳多樣性的時間可達200年,成為健康、有活力、可持續發展的種群。
大熊貓“肉肉”
熊貓守護者程建斌
當完“月老”當“月嫂”
程建斌是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臥龍神樹坪基地的飼養員。13年來,飼養管理的各個崗位,他都做過,不同年齡段的大熊貓,他都飼養過,近幾年來,他幾乎扎根神樹坪基地繁育園,全身心投入到大熊貓的繁殖工作。
在每年春節前后,參與繁殖工作的大熊貓們就陸續住進臥龍神樹坪基地的繁育園,等待著一場春天的戀愛。程建斌和同事們主要是作為大熊貓的“月老”,為適齡大熊貓們牽起“紅線”,為發情的雌性大熊貓找到“如意郎君”。“要觀察和監測它們的行為變化和激素變化,并根據這些變化,適時調整飼養管理方案,然后在最佳的時間,安排兩只大熊貓見面,在尊重大熊貓自然發情規律的前提下,讓它們進行自然交配。”程建斌已經見證一對對大熊貓們“喜結良緣”并幫助它們順利生產。
而在待產期和產后護理階段,飼養員還要隨時觀察母獸情況,及時做出飼養調整,保證母獸能順利生產和產后恢復,相當于我們常說的“月嫂”。大熊貓不會說話,無法用語言來溝通和表達,這就需要飼養員必須對大熊貓要有科學的認識,通過它們的行為、聲音、活動量等各方面的數據,并根據飼養經驗評估大熊貓不同階段的需求。“看到圈養大熊貓的種群逐漸壯大,讓我感到十分欣慰與自豪,說明我們的付出有了成果,希望這群黑白生靈能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大熊貓“叻叻”
熊貓博士王東輝
突破大熊貓人工繁育瓶頸
每年3月至5月,是大熊貓的“發情期”,也是提升大熊貓繁殖率、破解阻礙圈養大熊貓種群高質量發展瓶頸的關鍵時期。每年這個時候,也是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研究人員最忙碌的時候。
“大熊貓屬于單次季節性發情動物,一年只有一次繁殖機會,同時它的擇偶性非常強。”研究人員一方面要幫助大熊貓順利懷上寶寶,同時還要針對大熊貓繁育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開展有針對性的科學研究。王東輝是成都大熊貓繁育研究基地的一名“熊貓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大熊貓等瀕危野生動物生殖與繁育生物學。
經過近2年努力,王東輝和團隊科研人員在熊貓基地副主任侯蓉的帶領下,研發出了新型精液冷凍技術,發掘出更適合大熊貓精液冷凍保存的稀釋液。“為了保持圈養大熊貓種群的遺傳多樣性,需要依靠人工授精技術輔助繁殖,凍精質量是人工授精妊娠成功的關鍵因素。”在改良大熊貓精液冷凍技術的研究中,他們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如何使用珍貴稀少的樣本資源達到預期研究目標。經過閱讀海量文獻,縝密制定實驗方案,他們最終找到了程序更簡化、精子活力更高的解決方案。這一技術的正式投用,使大熊貓凍精質量提升了約10%。
隨著人工繁育大熊貓數量快速優質增長,大熊貓受威脅程度等級從“瀕危”降為“易危”,實現野外放歸并成功融入野生種群。作為具有野生大熊貓和圈養大熊貓資源的特大城市,近年來,成都持續大力推進大熊貓等瀕危野生動物保護研究,對大熊貓等珍稀瀕危動物的就地和遷地保護,以及遺傳資源保存作出了積極貢獻。如今,這些科研成果不僅應用到大熊貓保護上,還推廣應用到華南虎、小熊貓、丹頂鶴、綠尾虹雉、赤斑羚等其他珍稀瀕危野生動物的保護上。
-
 龍行龘龘 為何生僻字熱起來了?2024-02-06 18:05:07中國農歷龍年將至,龘字一躍火出了圈,成為生僻字界的扛把子,引起民眾關注和好奇。為何生僻字又熱起來了?從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24年春節聯
龍行龘龘 為何生僻字熱起來了?2024-02-06 18:05:07中國農歷龍年將至,龘字一躍火出了圈,成為生僻字界的扛把子,引起民眾關注和好奇。為何生僻字又熱起來了?從中央廣播電視總臺2024年春節聯 -
 被困高速3天3夜 小伙稱像人在囧途2024-02-06 17:57:352月6日消息,據國內多家媒體報道,從杭州駕車回重慶老家的駱先生,滯留高速公路3天3夜后,終于駛入暢通路段,跟家人團聚。駱先生表示:就像
被困高速3天3夜 小伙稱像人在囧途2024-02-06 17:57:352月6日消息,據國內多家媒體報道,從杭州駕車回重慶老家的駱先生,滯留高速公路3天3夜后,終于駛入暢通路段,跟家人團聚。駱先生表示:就像 -
 新郎接親被新娘親友堵樓下要中華煙 目擊者:新郎最終無奈答應2024-02-06 17:54:482月5日,江蘇淮安新郎接親遇女方親友鬧喜,被堵要求發30條中華煙,目擊者:新郎最終無奈答應。結婚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事關一生的大事,但是
新郎接親被新娘親友堵樓下要中華煙 目擊者:新郎最終無奈答應2024-02-06 17:54:482月5日,江蘇淮安新郎接親遇女方親友鬧喜,被堵要求發30條中華煙,目擊者:新郎最終無奈答應。結婚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事關一生的大事,但是 -
 外國醫生回應在武漢機場跪地救人 機場可用的儀器設備和積極的響應令人印象深刻2024-02-06 17:53:035日,武漢天河機場一老人突發心臟病,一外國醫生伸出援手急救。外國醫生回應:機場可用的儀器設備和積極的響應令人印象深刻。2月5日中午12
外國醫生回應在武漢機場跪地救人 機場可用的儀器設備和積極的響應令人印象深刻2024-02-06 17:53:035日,武漢天河機場一老人突發心臟病,一外國醫生伸出援手急救。外國醫生回應:機場可用的儀器設備和積極的響應令人印象深刻。2月5日中午12 -
 湖北新郎用8臺四驅拖拉機迎親 對你的愛就像拖拉機爬坡轟轟烈烈2024-02-06 17:43:05近日,道路結冰導致普通車輛難以通行,湖北一新郎用8臺拖拉機當婚車車隊迎娶新娘。網友評論:對你的愛就像拖拉機爬坡,轟轟烈烈。農村道路
湖北新郎用8臺四驅拖拉機迎親 對你的愛就像拖拉機爬坡轟轟烈烈2024-02-06 17:43:05近日,道路結冰導致普通車輛難以通行,湖北一新郎用8臺拖拉機當婚車車隊迎娶新娘。網友評論:對你的愛就像拖拉機爬坡,轟轟烈烈。農村道路 -
 霍建華李凱馨親密合照 感謝林心如的熱情招待2024-02-06 17:33:19霍建華全面開啟內地營業,目前和李凱馨主演新劇《他為什么依然單身》殺青,李凱馨曬出和霍建華以及林心如夫婦的合影,單獨和霍建華的合影引
霍建華李凱馨親密合照 感謝林心如的熱情招待2024-02-06 17:33:19霍建華全面開啟內地營業,目前和李凱馨主演新劇《他為什么依然單身》殺青,李凱馨曬出和霍建華以及林心如夫婦的合影,單獨和霍建華的合影引 -
 路面結冰小哥帶哈士奇送外賣 網友:這只狗的狗糧都是自己賺來的2024-02-06 17:31:172月3日,湖北地區遭遇大雪天氣,路面結冰,給人們的出行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位外賣小哥想出了一個獨特的辦法,他帶著一只
路面結冰小哥帶哈士奇送外賣 網友:這只狗的狗糧都是自己賺來的2024-02-06 17:31:172月3日,湖北地區遭遇大雪天氣,路面結冰,給人們的出行帶來了極大的不便。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位外賣小哥想出了一個獨特的辦法,他帶著一只 -
 光大證券:A股市場機會大于風險2024-02-06 17:29:42光大證券研報表示,從估值、股債性價比、換手率、融資交易占比等指標來看,當前A股市場或已處于底部位置,疊加當前政策積極發力,以股票型E
光大證券:A股市場機會大于風險2024-02-06 17:29:42光大證券研報表示,從估值、股債性價比、換手率、融資交易占比等指標來看,當前A股市場或已處于底部位置,疊加當前政策積極發力,以股票型E -
 直擊湖北高速:有人因暴雪滯留2024-02-06 17:28:24昨晚到今天,湖北全境出現了降雪天氣,部分地區出現大到暴雪。積雪深度可達10厘米以上,局部15厘米以上。此輪低溫雨雪冰凍天氣過程,將持續
直擊湖北高速:有人因暴雪滯留2024-02-06 17:28:24昨晚到今天,湖北全境出現了降雪天氣,部分地區出現大到暴雪。積雪深度可達10厘米以上,局部15厘米以上。此輪低溫雨雪冰凍天氣過程,將持續 -
 武漢暴雪兩只孔雀被凍在墻頂 已成功救下孔雀狀態良好2024-02-06 16:48:002月4日,武漢園一工人人員清除積雪時發現兩只孔雀被凍在墻頂,景區工作人員回應:已成功救下,孔雀狀態良好。2月4日,武漢園博園一工作人員
武漢暴雪兩只孔雀被凍在墻頂 已成功救下孔雀狀態良好2024-02-06 16:48:002月4日,武漢園一工人人員清除積雪時發現兩只孔雀被凍在墻頂,景區工作人員回應:已成功救下,孔雀狀態良好。2月4日,武漢園博園一工作人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