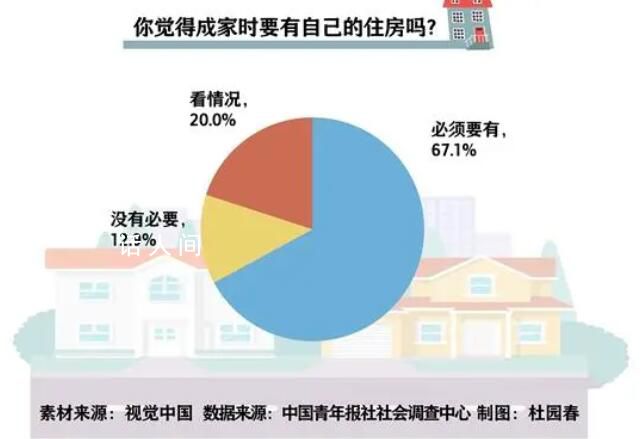青年外出打工3年被傳“已被槍斃” 農村碎嘴子現象已然有了相對普遍性和鮮明的社會性
導讀:春節期間走親訪友、網上沖浪之際,筆者關注到了農村 " 碎嘴子 " 現象的熱度以及大眾的普遍關注度,意識到該現象已然具有了相對普遍性和...

春節期間走親訪友、網上沖浪之際,筆者關注到了農村 " 碎嘴子 " 現象的熱度以及大眾的普遍關注度,意識到該現象已然具有了相對普遍性和鮮明的社會性。下面,筆者先舉數例以廓清該問題的社會表象:
城市打工青年 A 談到:" 我三年沒回家了,回去后才知道我一年前就因‘犯了事’被槍斃掉了 …… 三年間,我一直本本分分在外打工,卻被村里人‘說死了’,還是被槍斃,我比那竇娥還要冤!" 在外求學的 B 談到:" 前幾天有幾個鄰居來我家串門,問我現在在哪里,我說自己在 XX 省份的一所 985;結果鄰居次日就到處傳我在 XX 省份的酒吧里跳舞 ……" 網友 C 告誡廣大返鄉青年:" 早上最好不要在村里晨跑!今早我在村里跑了一圈,下午就被村里老人議論,說我大清早不知道從誰的被窩里跑出來了,忙慌地回家去。" 類似既可笑又可氣、令人哭笑不得的吐槽不計其數。有位十分幽默的網友總結道:一地的瓜子殼,把路過的人的一生都磕的稀碎;凡是路過,無一幸免!總的來看,這些社會現象具有一定的共性表征:事實被曲解,信息嚴重失真甚至被隨意篡改," 受害方 " 大多是青年人," 施暴者 " 大多是常住村里的中老年人。
春節期間,大批在外工作、求學的人們都選擇回鄉過年,這種選擇既是傳統,也是中國人的情結。這本是闔家團聚、重歸故里、歡度新春的好事,熱鬧事;但很多青年網友表示:返鄉后,需要面對鄉里鄉親、七大姑八大姨的 " 法術傷害 ",即 " 碎嘴子 " 的侵襲,簡直不勝其擾、快要瘋掉;為此,很多網友甚至打算來年春節不再返鄉過年。
或許是年輕人 " 玩梗 ",或許確有其事。但無論如何," 碎嘴子 " 都是一種負面的、貶義的口語化表達,意指交往行為的非理性,溝通方式的瑣碎化,語言內容的虛假性,交流途徑的非正式性等基本內涵。這是一種文化符號或標簽,人們常常以此回擊被議論、被嘲弄、被構陷的負面交往遭遇。" 碎嘴子 " 既有行為意義,指閑言碎語、無事生非、亂嚼舌根的活動;又有群體意義,特指經常性發生該行為的特定人群。
要想對農村 " 碎嘴子 " 現象的性質和影響進行社會定性,并非易事。往重了說,我們可以引證存在主義大師薩特的一句名言:他人即地獄。意指該現象對 " 受害者 " 的聲譽、心理和生活都造成了巨大影響,是極惡劣的語言傷害和社會行為,這簡直就是 " 網絡暴力 " 的現實表現;甚至可以上綱上線至 " 謠言罪 "。往輕了說,這不過是村里人過嘴癮、打發無聊的慣有做法,無關痛癢,不必過分理會。說重了,不至于,畢竟村里的閑言碎語往往局限在村域之中,并不會造成廣泛的負面社會影響,更談不上 " 定罪 ";說輕了,又太草率,畢竟人人都不想被詬病、被誣陷、被造謠,人人都有被承認、被尊重的心理需要。
客觀地說," 碎嘴子 " 現象并不僅僅存在于農村,凡是存在社會關系和行為的場域中都存在違背交往行為理性的現象。那么,為什么村里的這種現象表現得尤為明顯?筆者認為主要原因有二:
一方面,農村往往是一個相對獨立、狹小、封閉的場域,是一個彼此熟系的社會,人們關注的對象往往也是作為自己人的 " 村里人 "。因此,嚼舌根和被嚼舌根往往都是同村人,大家互相認識,互有來往;兩種社會群體甚至在角色上有時會發生轉變,進而 " 互相傷害 ",你說我,我說你,他又互相告知,沒完沒了 …… 所以,在此狹小的社會場域中," 被嚼舌根 " 的心理感應往往更直接、更快速、更切實。這也就是上面幾個案例中大多數人能夠快速(往往僅需半日)得知自己被談論的一大原因了。
另一方面,村里的人際交往存在一定的非理性,構成這種現象的因素具有相當的復雜性:人性之惡(有些村民確實看不得別人過得比自己好,進而構陷之,這被胡適說成人性中的 " 至惡 "),村民受教育水平有限、整體素質不高,接受及處理信息的能力不足(可能很多村里老人真的不懂什么是 985),等等。總之," 碎嘴子 " 行為的目的并不是進行真實信息的交換和校對,也不是為了促進彼此間的理解和友善交際;很多時候僅僅是在一種顢頇、孟浪、不負責任的交往狀態下草率地完成了語言和表情層面的交流和傳遞。
說到這里,還有一個問題亟待被解釋:為什么對 " 碎嘴子 " 具有較強感受的往往是常年不在村的青年人,久居農村、長期 " 被折磨 " 的人不該有更強的感受嗎?筆者認為,處理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一方面,從社會結構和生活模式的角度看,青年人的大多數時間都是生活在城市,過年返鄉只是當下生命階段的小部分時間。城市是一個陌生人社會,雖然人居密度要比農村大很多,但是 " 入住多年,仍不知鄰居姓甚名誰 " 的交往區隔是普遍存在的。進城多年的青年人逐漸適應了這種 " 無必要,不往來 " 的生活模式,并對村里人 " 瞎操心 " 的行為具有心理上的強烈拒斥。費孝通先生將傳統鄉村描述為 " 熟人社會 ",這種社會結構是村里老人一直生活著并適應了的,他們對 " 碎嘴子 " 現象逐漸脫敏并適應,甚至參與其中。有些受訪老人表示:" 甭看 ta 說我,誰要是說我,我大不了找個空子也說 ta"。然而,當下進城青年正處于中國城市化快速發展時期,雖然生在農村,但卻生活在城市。正是有了這種具有 " 過渡性 " 青年人的大量存在,以及農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涌入,傳統鄉村結構才實現了介于熟悉和陌生之間的 " 半熟人社會 " 的轉變。在此情況下,久居鄉村的老年人看返鄉的青年人總有些 " 看西洋鏡 " 式的心理,既好奇又不甚理解,而且總是傾向于用保守、老舊的眼光看待新事物、新行為。這也就是上述案例中很多老人把晨跑扭曲化看待的一大原因了。
另一方面,從鄉村文化的角度看,雖然青年人總會對村里的 " 碎嘴子 " 表示反感,但是這種反感卻往往不是認真的,不會真計較,即使被訛傳到 " 犯了事被槍斃 " 的地步也不會去告村里人 " 造謠罪 "。費孝通先生在《鄉土中國》中將這種遇事不追究的現象概括為傳統鄉村的 " 無訟 " 傳統,這種傳統仍然影響著當下鄉村生活。現實中,即使是涉及現實利益的官司都可以在鄉村中被私了、被消解," 碎嘴子 " 這種言語上的沖突更算不了什么。表面看這是一種文化包容,但似乎也意味著農村的 " 碎嘴子 " 具零成本、無責任的 " 自由 ",加劇了該現象的泛濫成災。
但是,村里的一位古稀老人說:" 咱村的碎嘴子總是那么幾個,大家都知道是誰,都離得他們遠遠的,不愿意跟他們共事。他們說的話,根本不著調啊!" 因此," 碎嘴子 " 們并非具有完全意義上的 " 犯罪 " 零成本,而受到鄉村社會道德體系的內在軟約束,并在其中逐漸失去了自身的社會資本和信譽,甚至被孤立、被邊緣化。在相對熟悉的生活交往中,村民總能輕易地對其進行群體性識別,并標簽化、疏遠之。正因如此,村民普遍認為 " 碎嘴子 " 們總是那小撮兒人。他們正是在 " 群分 " 的社會結構劃分基礎上,進行假信息、偽新聞的 " 炮制 " 和傳播,是村里不受待見的 " 信息員 "。更為重要的是,其余村民對這個特定群體的信息傳遞并不是聽之任之、盲目相信。村民們不但具有相當精準的判斷力,而且會選擇保持更加謹慎、更加質疑的態度,多數時候即使聽到了也不會相信,甚至會施加譴責。正是有了道德和人際的雙向約束," 碎嘴子 " 行為才不至于泛濫成災,鄉村社會中的是是非非也才能是可控的," 好好說話,好說話,說真話 " 才能是鄉村社會交往的主要模式," 睦鄰友好 " 的交往原則也才能一直被農民認可和接受。
總而言之,雖然村里離譜而又滑稽的閑言碎語帶給部分青年人很多心理和生活上的煩惱,但該回家過年還是得回家過年;多數時候應保持鈍感力,必要時也可以采取正確、可取的方式,給予適當澄清和說明。今年過年回家,你被 " 碎嘴子 " 了嗎?
下一篇:最后一頁
-
 青年外出打工3年被傳“已被槍斃” 農村碎嘴子現象已然有了相對普遍性和鮮明的社會性2024-02-16 09:59:34春節期間走親訪友、網上沖浪之際,筆者關注到了農村 " 碎嘴子 " 現象的熱度以及大眾的普遍關注度,意識到該現象已然具有了相對普遍性和
青年外出打工3年被傳“已被槍斃” 農村碎嘴子現象已然有了相對普遍性和鮮明的社會性2024-02-16 09:59:34春節期間走親訪友、網上沖浪之際,筆者關注到了農村 " 碎嘴子 " 現象的熱度以及大眾的普遍關注度,意識到該現象已然具有了相對普遍性和 -
 這一別不知何時相見了 年過完了離開家了2024-02-16 09:45:51春節假期16日開始將迎來返程高峰,網友們紛紛感慨:年過完了離開家了,這一別不知何時相見了。2月16日,這一別不知何時相見了的新聞穩居熱
這一別不知何時相見了 年過完了離開家了2024-02-16 09:45:51春節假期16日開始將迎來返程高峰,網友們紛紛感慨:年過完了離開家了,這一別不知何時相見了。2月16日,這一別不知何時相見了的新聞穩居熱 -
 濟南興洲解散 投資人與俱樂部對立2024-02-16 09:43:352月16日凌晨,中甲濟南興洲俱樂部發布官方聲明,因教練組內部工作分歧被自媒體爆出,導致投資人與俱樂部對立。濟南興洲決定退出中國足球職
濟南興洲解散 投資人與俱樂部對立2024-02-16 09:43:352月16日凌晨,中甲濟南興洲俱樂部發布官方聲明,因教練組內部工作分歧被自媒體爆出,導致投資人與俱樂部對立。濟南興洲決定退出中國足球職 -
 普京稱更希望拜登當選 特朗普回應2024-02-16 09:41:19當地時間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出席莫斯科未來技術論壇時接受的采訪引發關注。采訪中,普京首次稱更希望拜登當選美國總統,還稱美國國務卿
普京稱更希望拜登當選 特朗普回應2024-02-16 09:41:19當地時間14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出席莫斯科未來技術論壇時接受的采訪引發關注。采訪中,普京首次稱更希望拜登當選美國總統,還稱美國國務卿 -
 外甥抱住舅舅女朋友吵鬧要帶回家 表現出強烈的依戀之情2024-02-16 09:39:46在這個春節的河南了家庭聚會上,發生了一件既有趣又感人的事情。一個小外甥第一次見到了他舅舅的新女朋友,并對這位女士表現出了極大的喜愛
外甥抱住舅舅女朋友吵鬧要帶回家 表現出強烈的依戀之情2024-02-16 09:39:46在這個春節的河南了家庭聚會上,發生了一件既有趣又感人的事情。一個小外甥第一次見到了他舅舅的新女朋友,并對這位女士表現出了極大的喜愛 -
 薛之謙《飛馳2》影評被指盜攝 粉絲:所用照片均出現在宣傳片中2024-02-16 09:37:322月15日,薛之謙在社交平臺分享了觀看電影《飛馳人生2》的觀后感卻被指盜攝;粉絲:所用照片均出現在宣傳片中。韓寒導演的《飛馳人生2》上映
薛之謙《飛馳2》影評被指盜攝 粉絲:所用照片均出現在宣傳片中2024-02-16 09:37:322月15日,薛之謙在社交平臺分享了觀看電影《飛馳人生2》的觀后感卻被指盜攝;粉絲:所用照片均出現在宣傳片中。韓寒導演的《飛馳人生2》上映 -
 “文旅大餐”豐富百姓假期生活 文旅景點客流顯著增長2024-02-16 09:35:202024春節全國多地旅游市場火爆,文旅景點客流顯著增長。各地文旅大餐不僅豐富了百姓假期生活,也有利于釋放消費新動能。2024年春節長假帶火
“文旅大餐”豐富百姓假期生活 文旅景點客流顯著增長2024-02-16 09:35:202024春節全國多地旅游市場火爆,文旅景點客流顯著增長。各地文旅大餐不僅豐富了百姓假期生活,也有利于釋放消費新動能。2024年春節長假帶火 -
 新疆發布暴雪大風寒潮紅色預警 請大家做好防范2024-02-15 21:08:022月15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氣象臺陸續發布暴雪、大風、寒潮紅色預警信號,請大家做好防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氣象臺2024年2月15日10時28分發
新疆發布暴雪大風寒潮紅色預警 請大家做好防范2024-02-15 21:08:022月15日,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氣象臺陸續發布暴雪、大風、寒潮紅色預警信號,請大家做好防范。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氣象臺2024年2月15日10時28分發 -
 馬克龍和澤連斯基將簽署安全協議 該協議的具體細節并未披露2024-02-15 21:05:45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訪問巴黎期間,烏克蘭與法國將簽署安全保障協議。正如《歐洲真相》所寫,這是美聯社參考愛麗舍宮聲明報道的。該協議的具
馬克龍和澤連斯基將簽署安全協議 該協議的具體細節并未披露2024-02-15 21:05:45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訪問巴黎期間,烏克蘭與法國將簽署安全保障協議。正如《歐洲真相》所寫,這是美聯社參考愛麗舍宮聲明報道的。該協議的具 -
 近期厚衣服不要著急收 多地將上線冷暖大反轉2024-02-15 21:04:1417日起,寒潮將席卷我國大部分地區,帶來明顯降溫,多地將上線冷暖大反轉,厚衣不要著急收。即將到來的17日,我國將迎來一股強勁的寒潮,預
近期厚衣服不要著急收 多地將上線冷暖大反轉2024-02-15 21:04:1417日起,寒潮將席卷我國大部分地區,帶來明顯降溫,多地將上線冷暖大反轉,厚衣不要著急收。即將到來的17日,我國將迎來一股強勁的寒潮,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