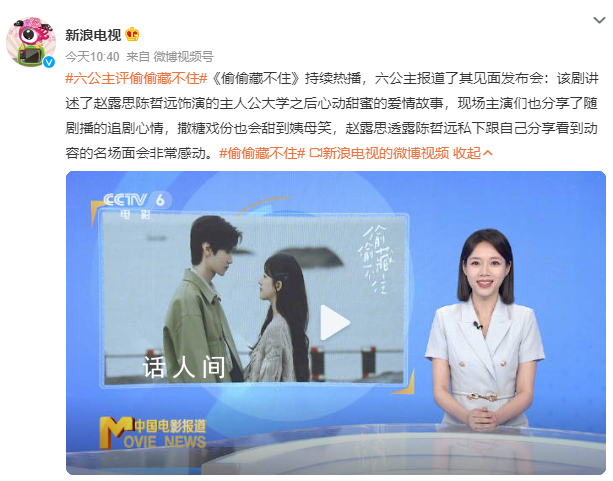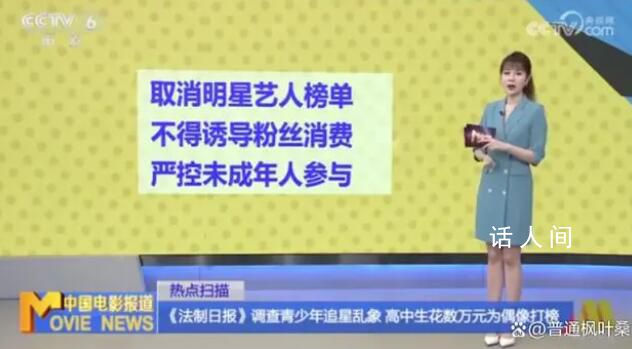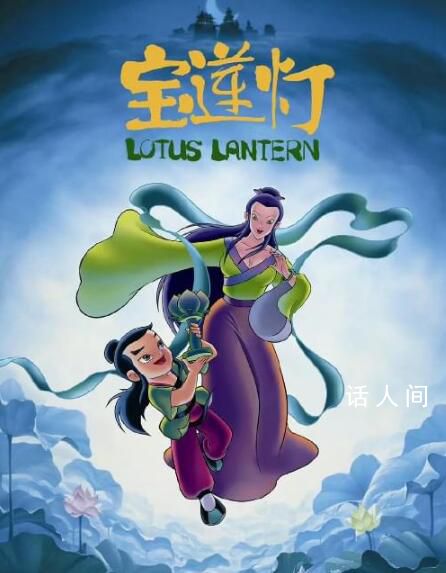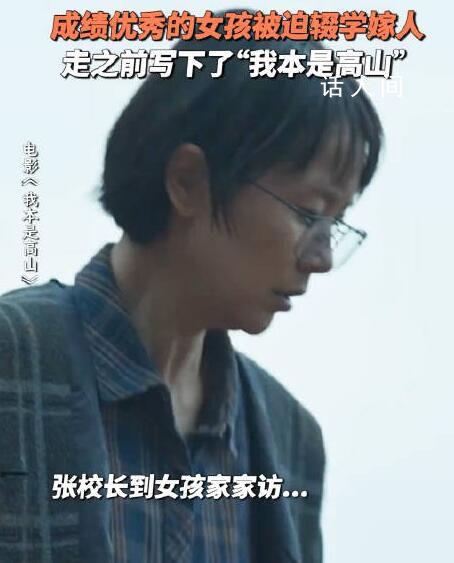六公主評周處除三害 黑色幽默港式黑幫臺式怪誕完美混搭
導讀:3月2日,CCTV6評電影《周處除三害》:黑色幽默港式黑幫臺式怪誕完美混搭,引發關注。電影《周處除三害》帶來一個典故的再次傳播:見于《晉...
3月2日,CCTV6評電影《周處除三害》:黑色幽默港式黑幫臺式怪誕完美混搭,引發關注。

電影《周處除三害》帶來一個典故的再次傳播:見于《晉書·周處傳》和《世說新語》的這一故事,說的是晉人周處是招人嫌的浪蕩子,被鄉人與水中蛟龍、山上白額虎一起稱為“三害”。后在別人慫恿之下,他下河斬龍、上山打虎,除掉二害之后,發覺自身之惡,從此改過自新。
電影直接把這個故事拿來改編成“犯罪動作電影”,核心創意沒變,呈現形式有變,蛟龍和惡虎在片中變成了通緝令上榜一香港仔和榜二林祿和,而位居榜三的“當代周處”陳桂林,則模仿晉人周處,想通過除掉前兩害,達到青史留名的目的。在行為動機方面,電影和典故有微妙的差別,周處是在眾人慫恿的前提下被動出發的,而陳桂林則是為了證實自身價值主動出擊的。當然,兩者因為終極目標相同,其行為動機的那點差別也就顯得不那么重要了。
電影中的香港仔身上有蛇的刺青,林祿和背后有鷹的刺青,這是反面人物的典型標志,而陳桂林身上也有兩個鮮明的標志,一是手腕上戴的奶奶去世后留下來的兒童手表,二是眉骨處被香港仔用剃刀割出的傷疤,這兩個標志其實已清晰地表達出創作者的意圖:陳桂林不但備受老人疼愛,還有一顆童心,他的“兇惡”面相,是外部環境造就。可以說,經過這一番“洗白”,陳桂林已經大面積脫離了古典著作中對原型周處的定義,而有了別樣的寓意。
用當下眼光來解讀,“萌兇”的陳桂林,他的拳腳與槍支,所指向的已經并非他的刺殺對象,而是對自己所處環境與社會的一種反擊與抗爭。當地的幫派之惡,經由電影中發廊女程小美的遭遇折射,令人頓生厭惡;充滿愚蠢、欺騙、邪惡的靈修騙局,則是人心空洞、失落、無望的表現,陳桂林對幫派頭子、靈修大師和其死忠粉的大開殺戒,已經脫離了對個體的懲戒,而成為對整體的討伐。這樣的討伐,使得電影的批判意義得以實現。
從片頭到片尾,《周處除三害》都在表達陳桂林的自我凈化過程:對程小美的解救、殺香港仔、識破靈修騙局、打電話給警察陳灰投案自首、獄中接受程小美的修面理發……隨著情節每進展一步,陳桂林的心靈塵霾便被掃除一片。由此便不難理解,他被戴上手銬后面對無數攝像機會露出如此燦爛的笑容。因為通過這一連串的“大掃除”,他已經回到了正常人的行列,從秩序的破壞者變成了維護者。而影片令人震撼的段落,當屬對靈修騙局進行揭示,陳桂林在受騙后接受所謂的“尊者”鞭打時的痛哭流涕,那確實是他最為接近洗心革面的關鍵時刻,痛悔與救贖也在那刻達到一個頂峰。不過,諷刺與荒誕的是,這樣的徹悟,居然是由一個騙子集團所帶來的。
《周處除三害》有著對“骯臟”與“干凈”的反復類比,作為從“糞坑”中想要奮力跳出來的人,陳桂林幾乎使用了能把自己洗刷干凈的所有辦法,影片留有不少細節來表現陳桂林對于“干凈”的渴望,比如,對那枚兒童手表的珍愛,對程小美沒有言說的愛意,對陳灰的服從與敬意,乃至伏法時眼神中的坦然,這些“大男孩”式塑造手法,最終讓古典著作中的周處成了更具豐富性的當代陳桂林。
與其說觀眾是被這部電影所謂的“尺度之大”所吸引,不如說影片的內核更具感染人的力量,情節與人物,畫面與音樂,這些都是在為影片的內核所服務。如果只看到影片中淺層的表達,而沒有覺察到故事最內里的深沉,那么等于沒有看見《周處除三害》的改編價值。這部電影的受歡迎,并非因為“噱頭”,而是因為人對正義、干凈、善良本能的向往。
用最溫婉的歌(《新造的人》)來映襯最邪惡的惡,用最直接的報復來破壞與重建,這是《周處除三害》的亮點。同時,影片也存在情節轉折方面的一些粗糙,比如陳桂林路過時恰好聽見靈修騙局等,但這些缺憾沒有給影片整體氣質造成太大的影響,在觀感的連貫性、表達的深刻性、寓意的延展性等方面,《周處除三害》都有不少可取之處。
下一篇:最后一頁
-
 六公主評周處除三害 黑色幽默港式黑幫臺式怪誕完美混搭2024-03-03 16:29:053月2日,CCTV6評電影《周處除三害》:黑色幽默港式黑幫臺式怪誕完美混搭,引發關注。電影《周處除三害》帶來一個典故的再次傳播:見于《晉
六公主評周處除三害 黑色幽默港式黑幫臺式怪誕完美混搭2024-03-03 16:29:053月2日,CCTV6評電影《周處除三害》:黑色幽默港式黑幫臺式怪誕完美混搭,引發關注。電影《周處除三害》帶來一個典故的再次傳播:見于《晉 -
 焉栩嘉在郝蕾面前提到鄧超 讓現場氣氛瞬間升溫2024-03-03 16:25:03《無限超越班2》的一幕成為了眾人矚目的焦點,其中,焉栩嘉的一句話讓現場氣氛瞬間升溫。他提到了鄧超,那個在電影《影》中留下深刻印象的
焉栩嘉在郝蕾面前提到鄧超 讓現場氣氛瞬間升溫2024-03-03 16:25:03《無限超越班2》的一幕成為了眾人矚目的焦點,其中,焉栩嘉的一句話讓現場氣氛瞬間升溫。他提到了鄧超,那個在電影《影》中留下深刻印象的 -
 董明珠:年輕人不能為掙錢而活 把掙錢當成夢想就會不擇手段2024-03-03 16:23:00近日,格力董事長董明珠在接受采訪時稱年輕人不能為掙錢而活:把掙錢當成夢想,就會不擇手段。話人間3月3日消息,在日前播出的央視財經《對
董明珠:年輕人不能為掙錢而活 把掙錢當成夢想就會不擇手段2024-03-03 16:23:00近日,格力董事長董明珠在接受采訪時稱年輕人不能為掙錢而活:把掙錢當成夢想,就會不擇手段。話人間3月3日消息,在日前播出的央視財經《對 -
 53歲媽媽給25歲女兒生了個弟弟 全家人都很開心2024-03-03 16:19:00據媒體報道,3月1日,黑龍江一位53歲的母親給25歲的女兒生了個小弟弟,引發網友熱議。女兒:很激動,全家人都很開心。在這個充滿奇跡的世界
53歲媽媽給25歲女兒生了個弟弟 全家人都很開心2024-03-03 16:19:00據媒體報道,3月1日,黑龍江一位53歲的母親給25歲的女兒生了個小弟弟,引發網友熱議。女兒:很激動,全家人都很開心。在這個充滿奇跡的世界 -
 特斯拉跑車100公里加速不到1秒 預計明年開始發貨2024-03-03 16:15:01日前,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宣布,特斯拉新一代Roadster跑車的生產設計已完成,將在年底推出,預計明年開始發貨。馬斯
特斯拉跑車100公里加速不到1秒 預計明年開始發貨2024-03-03 16:15:01日前,特斯拉首席執行官埃隆·馬斯克在社交媒體上宣布,特斯拉新一代Roadster跑車的生產設計已完成,將在年底推出,預計明年開始發貨。馬斯 -
 當中國商船在太平洋遇到祖國航母 這是來自于人民的真切激勵2024-03-03 16:12:32山東艦,你好。在太平洋上,能遇到祖國的航母在此訓練,我感到非常自豪,為祖國繁榮昌盛,感到無比興奮!中國船長看到山東艦激動喊話,山東
當中國商船在太平洋遇到祖國航母 這是來自于人民的真切激勵2024-03-03 16:12:32山東艦,你好。在太平洋上,能遇到祖國的航母在此訓練,我感到非常自豪,為祖國繁榮昌盛,感到無比興奮!中國船長看到山東艦激動喊話,山東 -
 港星張致恒貼收款碼求網友捐款 請求外界捐款來幫助他渡過難關2024-03-03 16:10:47近日,香港男星張致恒因陷入經濟困境,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張收款碼,請求外界捐款來幫助他渡過難關。香港知名男星張致恒(Steven)近期頻繁
港星張致恒貼收款碼求網友捐款 請求外界捐款來幫助他渡過難關2024-03-03 16:10:47近日,香港男星張致恒因陷入經濟困境,在社交媒體上發布了一張收款碼,請求外界捐款來幫助他渡過難關。香港知名男星張致恒(Steven)近期頻繁 -
 女子故意不接快遞電話以索賠獲利 非法獲利37,000余元2024-03-03 16:09:002021年至2023年期間,女子彭某以投訴索賠為目的,網購大量生鮮類商品后故意不接快遞電話或接通后假裝聽不見,促使快遞員先簽收后派送,隨后
女子故意不接快遞電話以索賠獲利 非法獲利37,000余元2024-03-03 16:09:002021年至2023年期間,女子彭某以投訴索賠為目的,網購大量生鮮類商品后故意不接快遞電話或接通后假裝聽不見,促使快遞員先簽收后派送,隨后 -
 新規后快遞員業務量狂增十幾倍 狂奔的快遞員最擔心投訴件增多2024-03-03 16:07:013月1日,新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施行首日,風濤起得比往常早,經歷了短暫的培訓,上崗第一天他有點兒興奮和緊張。揀件、裝車、致電、
新規后快遞員業務量狂增十幾倍 狂奔的快遞員最擔心投訴件增多2024-03-03 16:07:013月1日,新修訂的《快遞市場管理辦法》施行首日,風濤起得比往常早,經歷了短暫的培訓,上崗第一天他有點兒興奮和緊張。揀件、裝車、致電、 -
 曹縣人在家一天能做200條馬面裙 從賣辣椒到馬面裙利潤翻了十倍不止2024-03-03 16:01:11繼馬面裙成新春戰袍并熱賣3個億后,400名大學生回曹縣小鎮賣馬面裙再次登上熱搜。曹縣,這個近年來頻繁進入大家視野的山東小縣城,如今正與
曹縣人在家一天能做200條馬面裙 從賣辣椒到馬面裙利潤翻了十倍不止2024-03-03 16:01:11繼馬面裙成新春戰袍并熱賣3個億后,400名大學生回曹縣小鎮賣馬面裙再次登上熱搜。曹縣,這個近年來頻繁進入大家視野的山東小縣城,如今正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