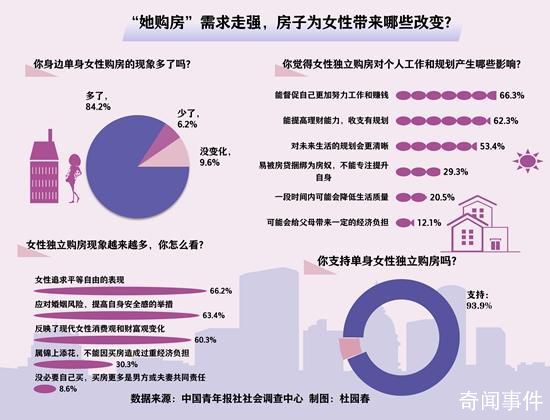女性平均被家暴35次才會報警 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次
導讀:中國在建立反家暴社會支持體系的過程中,經歷著觀念、制度、體系的撕扯與磨合。對家暴零容忍已成社會共識,但在每一個具體個案中,反家暴推
中國在建立反家暴社會支持體系的過程中,經歷著觀念、制度、體系的撕扯與磨合。對家暴“零容忍”已成社會共識,但在每一個具體個案中,“反家暴”推動者們看到的是受害者復雜的生存困境。

家暴,只有零次和無數次。
過去一年,由北京市東城區源眾家庭與社區發展服務中心(以下簡稱“源眾服務中心”)運營的“家暴求助”微信小程序,共收到1117條在線咨詢,完成了6000余次危險性自評,其中,家庭暴力占到總求助量的90%左右,未成年人咨詢占比30%。
每天早上,源眾服務中心項目官員王卓盈會將前一天的所有在線咨詢內容導出,包括個人信息、家庭暴力類型、最近一次發生家暴的時間、受家暴時長等,歸納梳理至Excel后,再發到志愿者律師群,待他們進行回訪。
在回訪過程中,大部分咨詢者留下的電話號碼根本無法接通,有的人會等律師自我介紹結束后掛斷電話,有的人會直接拒絕添加微信好友,有的人即使添加為好友,也會表示暫時不用回訪了……最終可以形成心理咨詢、法律援助的個案僅占全部咨詢的3%。
“當惡性家暴事件在網絡上迅速發酵時,家暴求助小程序的訪問量就會迅速增加,電話咨詢也會隨即變多。”王卓盈說。然而,“難以離開”是家庭暴力的特征之一,也是處理家暴個案的難點之一。
家庭暴力是暴力行為,
是一種權力控制
今年3月,劉小曉與前夫協議離婚后,在商談財產分割問題時,遭到前夫的暴力毆打,導致膝關節前交叉韌帶斷裂,雙腿無法行走。劉小曉告訴王卓盈,她的主要訴求是要求前夫賠付所有醫療費用,并完成離婚財產分割,歸還屬于她的個人財產。
截至7月末,劉小曉的雙膝已經經歷了大大小小共7次手術。“4月19日,劉小曉收到傷情鑒定書,經司法鑒定為輕傷二級,在當地派出所完成筆錄后,民警卻建議雙方當事人調解。”王卓盈表示,一般情況下,只有公安機關立案,才能進入司法程序。
在具體的家暴案件推進過程中,人為推動很重要。為了幫劉小曉推動案件進展,王卓盈和負責的律師決定前往當地,與派出所民警進行溝通——必須得立案。
王卓盈入行一年。她原本以為法律如何規定,相關部門便如何執行,但事實并非如此,法律規定與公檢法實踐之間確實存在鴻溝。比如,遭受精神暴力的人去報警,雖然法律上有所規定,但很可能達不到行政處罰的標準;一些家庭暴力行為,被認定為夫妻矛盾、家庭糾紛,只能一次次調解;一些地方法院,至今也無法出具家暴受害者申請的人身安全保護令。
源眾服務中心創始人李瑩說:“家庭暴力是暴力行為,是一種權力控制。而家庭糾紛也許有暴力行為,但可能是偶發的、沖動之下的推搡,不會特別嚴重。兩者最大的區別,是夫妻雙方的關系是否平等。”家庭暴力與家庭糾紛的表現形式和權力關系,完全不同。
美國家暴咨詢專家倫迪·班克羅夫特在《他為什么打我:家庭暴力的識別與自救》中寫道:“‘家暴’一詞,關乎權力。”意思是,某人利用力量的不平衡去剝削和控制別人。只要存在力量不平衡,比如男人和女人之間、大人和小孩之間,或者富人和窮人之間,有些人就會利用家暴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由此看出,如果夫妻正在經歷嚴重的家暴,并形成了暴力循環,一味調和,可能會給當事人帶來很大的人身安全風險。
很多人認為這是“家務事”,
向外界求助充滿恥感
在家暴求助小程序上,咨詢者可以通過危險性自評,判斷自己的處境。危險性自評的結果分為高危、中危、低危三個等級,小程序會根據測試結果給用戶對應的建議。“高危”建議盡快尋求外部幫助,“中危”要建立應對意識、開始采取措施,“低危”是建立有效溝通方式。
除了自評,王卓盈也會通過用戶在線咨詢里的自述、受家暴時長和最近一次發生家暴的時間來綜合判斷家暴的危險性。對于危險級別較高的咨詢者,她會優先安排律師進行回訪。
然而,“只有非常堅定要與施暴者分開的人,或者本身對家暴敏感度比較高的人,才會接受律師的回訪”。
王卓盈認為,大部分咨詢者最終選擇拒絕回訪的原因是,家暴發生后不久,施暴者會進行道歉,兩個人重歸于好,進入蜜月期。大部分受害者在非必要情況下,并不愿意回憶被家暴的經歷。
李瑩在《走到春暖花開:一位女律師辦案手記》中提及的冬梅與丈夫田強、山桃與丈夫盧旺、杜鵑與丈夫王大川等人,都循環往復地經歷著家暴的三個階段,即矛盾爆發期、蜜月期和矛盾聚集期。
丈夫因為無關緊要的事情對妻子大打出手,二人進入矛盾爆發期;等情緒宣泄完,他再回過頭向妻子道歉認錯,兩人重歸于好;好景不長,夫妻雙方會再次出現輕微的摩擦和暴力,直到矛盾再次爆發,進入矛盾聚集期。這種循環式的家暴,嚴重程度會逐漸升級。
家暴的本質是一種長期的、反復的、系統性的行為。如果一個家庭沒有在第一次發生家暴時有效應對,家暴可能就會無數次地發生。
截至7月底,家暴求助小程序共收到1117條在線咨詢,而源眾服務中心向求助者提供的緊急生活救助金、緊急心理支持和緊急法律援助,卻僅占咨詢量的3%。
關于求助咨詢數與最終形成的個案數相差甚大,李瑩在采訪中表示,這種“倒三角”情況反映了家庭暴力求助的艱難性,很多人依然認為這是“家務事”,向外界求助時會有恥感。
這種恥感的產生基于傳統的家庭觀念、個人對于家暴不自覺的恐懼,以及親密關系中的難以啟齒,這是一種復雜且矛盾的內在感受。
很多經歷家庭暴力的人,
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虐待
27歲的張琦,在過去一年里多次遭到前夫對她的暴力行為,先是辱罵、推搡,再到暴力毆打。兩人離婚后,前夫還不止一次求原諒,張琦有過動搖,直到有一次兩人逛街時,前夫再次將她推倒在地,并動手打了她。
張琦將被打的遭遇告訴父母,表示想報警。她得到的卻是父母的否定——不想將事情鬧大。她鼓足勇氣去報警,民警認為這屬于伴侶鬧矛盾,并未出具告誡書,但當面批評、教育了前夫。至此,兩人才徹底分開。
在對家暴的認定中,不僅公權力存在不確定性,處于家暴中的受害者的生活環境、父母的觀念、周圍人的意識,也會影響他們的判斷。對于家暴行為的認定,一部分家暴受害者甚至需要反復從外界獲得確認。
“這樣的經歷到底算不算家暴?”這是在家暴求助小程序的后臺,詢問最多的問題。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以下簡稱《反家庭暴力法》)中的解釋,明確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之間以毆打、捆綁、殘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經常性謾罵、恐嚇等方式實施的身體、精神等侵害行為。
大多數經歷家庭暴力折磨的人,很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正在遭受虐待。調查顯示,面對家暴,女性平均被虐待35次才選擇報警。
一直以來,公權力如何介入家庭關系,存在很多說法。有人認為“清官難斷家務事”,因家庭作為公民的私人空間,傳統觀念認為公權力一般不便過多干預;也有人認為,公權力的過多介入,有可能激化夫妻矛盾。
王卓盈在協助解決家暴個案的過程中,常常會發現民警不愿開告誡書,法院不愿出具人身安全保護令,一些律師對當事人(受暴者)所處的多重困境是漠視的,也很難理解當事人常常表現出來的糾結、搖擺和退縮。
李瑩在采訪中表示,她會送法官《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希望他們能看到身處男權壓制下的女性的真實處境;也會送上野千鶴子的《始于極限》《快樂上等》給律師朋友和心理咨詢師,因為只有建立更加開放的性別觀念,他們才能在受害者找上門時,提供所需要的支持。
任何法律制度的推廣與應用,都伴隨著學習、理解、適用的過程。《反家庭暴力法》剛實施時,李瑩和她的團隊一直致力于對公安、婦聯、律師、社工等全國各地基層執法人員進行培訓,培訓內容包括專業的家庭暴力知識、社會性別觀念等。
受害者平均要有7次反復,
才有可能徹底擺脫暴力關系
有網友說,自己的母親二婚后,被打了20年,他也被打,于是結婚后帶著母親一起生活。不承想母親又跑回丈夫的家,結果再次被打,鬧得全村人都知道了,大家報警,找村干部、找婦女主任,然而最后母親還是原諒了丈夫,但網友表示自己不會原諒。也有網友表示,曾幾何時,自己非常看不起和母親一樣遭受家暴且長時間隱忍的女人,不明白她們為什么沒有骨氣離開……
在《走到春暖花開:一位女律師辦案手記》中,李瑩提到了冬梅的故事。2016年,因為遭受丈夫家暴,冬梅抱著3歲的孩子從家里逃了出來,李瑩幫助冬梅申請到首個人身安全保護令,并幫助她順利完成訴訟離婚,幫她找到合適的出租房,婦聯也幫孩子辦理了轉學。但沒過多久,冬梅又回到前夫身邊。
李瑩說:“從源眾服務中心大量的個案情況來看,大部分遭受家暴的受害者會選擇繼續留在婚姻里。無論她是撤訴,還是復婚,我們都會尊重本人的真實意愿,理解她的選擇。因為我們不是她,她最后的選擇,有她的理由。”
為什么家暴受害者難以離開?李瑩在自己的書中寫到,這與受害者面臨的多重困境有關,也與特殊的心理狀態有關。在大眾認知里,家暴往往被認為是小事,是家丑,家丑不可外揚,這些觀念像枷鎖一樣禁錮了她們的思想;家暴受害者缺乏家人和朋友的支持,又很久沒有工作,如果離婚,沒法養活自己和孩子;還有人是為了孩子,認為孩子不能沒有爸爸——單親家庭很多時候會受歧視;她們甚至會受到威脅,如果想再婚,施暴者就揚言要殺害其全家。當然,也有公權力介入乏力、支持不足的原因。這些原因往往交織存在,讓她們陷入現實的困境里。
美國臨床心理學家雷諾爾·沃科在對數百名受家暴女性進行研究后發現,很多經受家暴的婦女會因為習得性無助,變得難以離開施暴者。雷諾爾·沃科將這種特殊的心理與行為模式稱為“受虐婦女綜合征”。
李瑩說:“長期遭受家暴的女性一直處于恐懼、焦慮、無助、認命的精神狀態里,內心處于一種癱瘓狀態,她們會不自主地強化對方的能力,矮化自己的能力,沒有辦法客觀地認識現實狀況。”
另外,長期遭受家暴者還會出現斯德哥爾摩綜合征。李瑩解釋說:“劫匪與人質在相處的過程中,雙方的心理會發生變化,人質會理解劫匪,會認同劫匪,如果劫匪有一些非常溫情的行為,人質會很感動,以失去理性的狀態對待劫匪。”
研究顯示,受害者平均要有7次反復,才有可能徹底擺脫暴力關系。
就像電影《消失的她》中,沈曼對李木子說:“你不要相信一個賭徒會改。”李瑩說,同樣,施暴者也不會主動停止暴力行為。
反家暴,需要建立多機構聯動的社會支持體系
在具體的家暴個案中,如果受害者需要法律支持,王卓盈首先判斷家暴受害者是否存在傷情,如果有,先取證——去醫院檢查,拍傷情照片,將其作為固定證據進行保密式保存。她會告訴受害者先下載網盤,上傳照片后設置為私密狀態,并設置密碼。
2016年后,源眾服務中心將服務調整為以法律援助為核心的綜合性支持模式,同時提供法律咨詢、法律援助、醫療救助、心理支持、生活救助等多方面的支持服務。
“反家暴是一個系統工程,一家機構無法解決家暴受害者的所有問題。”李瑩認為,反家暴需要建立一個多機構聯動的社會支持體系,這里面涉及派出所、社區、法院、檢察院、司法局、醫院、學校、民政、專業性社會服務機構等多機構、多部門的支持。而當下,中國反家暴的聯動機制并沒有有效建立起來,庇護機制也沒有被有效激活。
《反家庭暴力法》中明確表明,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負責婦女兒童工作的機構,負責組織、協調、指導、督促有關部門做好反家庭暴力工作。然而現實情況是,婦聯沒有行政執法權力,調動各部門的能力很有限。在具體的聯動機制中,以什么樣的方式聯動?誰來牽頭?如何配合?結案標準是什么?
目前國內各地區的庇護所大多設立在救助站,可提供10日的庇護,但地點偏僻,也無法提供專業性的服務,入住門檻較高,知曉度非常低。而在美國的庇護所,遭受暴力的女性可以在庇護所居住3—24個月,并得到綜合性的庇護,包括法律援助、心理支持、就業培訓等。
李瑩從2002年開始關注婦女兒童權益,受理了500起與家庭暴力、性騷擾、撫養權有關的案件。作為中國反家暴的見證者與推動者之一,她感受到大眾對家暴“零容忍”的社會共識已經形成;在具體的家庭暴力案件辦理過程中,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時間大大縮短,現在最快僅需6小時;公安機關出具家庭暴力告誡書的數量也明顯增多。另外,部分城市成立了婦女和少年兒童權益保障專業化人民法庭,法官的理念、專業性、專業水平更高。
-
 攀枝花公園豹子胖成了“豹警官” 年紀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2024-03-07 21:07:32近日,四川攀枝花公園內一只圓潤的金錢豹走紅,網友調侃稱胖成了豹警官,引發關注。園方回應:年紀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近日,攀枝
攀枝花公園豹子胖成了“豹警官” 年紀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2024-03-07 21:07:32近日,四川攀枝花公園內一只圓潤的金錢豹走紅,網友調侃稱胖成了豹警官,引發關注。園方回應:年紀大鍛煉少看起來胖,體檢正常。近日,攀枝 -
 多家金店足金報價突破650元每克 黃金的價格又漲了2024-03-07 21:05:30近日,國際金價連續上漲,黃金飾品價格也一漲再漲。截至7日上午,多家品牌金店的價格足金價格已經突破了650元 克。一覺醒來,黃金的價格又
多家金店足金報價突破650元每克 黃金的價格又漲了2024-03-07 21:05:30近日,國際金價連續上漲,黃金飾品價格也一漲再漲。截至7日上午,多家品牌金店的價格足金價格已經突破了650元 克。一覺醒來,黃金的價格又 -
 2024福布斯中國杰出商界女性 周群飛喻麗麗上榜2024-03-07 21:03:13今日,福布斯中國發布2024杰出商界女性100榜單,這是福布斯中國第10次發布該榜單,通過這份榜單可以看到中國商業世界的女性群像。其中,上
2024福布斯中國杰出商界女性 周群飛喻麗麗上榜2024-03-07 21:03:13今日,福布斯中國發布2024杰出商界女性100榜單,這是福布斯中國第10次發布該榜單,通過這份榜單可以看到中國商業世界的女性群像。其中,上 -
 呼倫貝爾現“寒夜燈柱”現象 場面奇幻而震撼2024-03-07 20:59:026日凌晨,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夜空中出現寒夜燈柱現象。夜色中一束束光柱直沖蒼穹,場面奇幻而震撼。雖已過驚蟄,但位于中國北疆的內蒙古呼
呼倫貝爾現“寒夜燈柱”現象 場面奇幻而震撼2024-03-07 20:59:026日凌晨,呼倫貝爾市海拉爾區夜空中出現寒夜燈柱現象。夜色中一束束光柱直沖蒼穹,場面奇幻而震撼。雖已過驚蟄,但位于中國北疆的內蒙古呼 -
 蔡瀾上海餐廳菜品有異物被罰5萬 有顧客在菜品中吃出異物2024-03-07 20:55:49近日,蔡瀾上海餐廳因生產經營混有異物的食品,被上海市黃浦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5萬元,引發關注。據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站近日消息,
蔡瀾上海餐廳菜品有異物被罰5萬 有顧客在菜品中吃出異物2024-03-07 20:55:49近日,蔡瀾上海餐廳因生產經營混有異物的食品,被上海市黃浦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5萬元,引發關注。據上海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網站近日消息, -
 兩男子起沖突被各自妻子緊緊抱住 家有賢妻禍事少2024-03-07 20:54:056日,有網友發視頻稱,北京兩男子街頭起沖突,雙方妻子死死抱住制止。目擊者表示:其中一位妻子被丈夫抱摔草里兩次都沒松手。家有賢妻禍事
兩男子起沖突被各自妻子緊緊抱住 家有賢妻禍事少2024-03-07 20:54:056日,有網友發視頻稱,北京兩男子街頭起沖突,雙方妻子死死抱住制止。目擊者表示:其中一位妻子被丈夫抱摔草里兩次都沒松手。家有賢妻禍事 -
 北京未開放個人申領三代社保卡 后續將逐步啟動2024-03-07 20:51:52近期,有群眾咨詢如何領取第三代社保卡,對此,3月7日,北京市人社局發出溫馨提示,當前,本市第三代社保卡換發工作正在分批次進展中。自今
北京未開放個人申領三代社保卡 后續將逐步啟動2024-03-07 20:51:52近期,有群眾咨詢如何領取第三代社保卡,對此,3月7日,北京市人社局發出溫馨提示,當前,本市第三代社保卡換發工作正在分批次進展中。自今 -

-
 女性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2024-03-07 20:46:45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月經不調可能會引發嚴重疾病嗎?知名專家在線互動解決你的問題。月經是女性生殖健康晴雨
女性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2024-03-07 20:46:45生理期不適該怎么辦?為什么我會感到特別疲倦和困乏?月經不調可能會引發嚴重疾病嗎?知名專家在線互動解決你的問題。月經是女性生殖健康晴雨 -
 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生5.5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2024-03-07 20:42:04據中國地震臺網正式測定,3月7日18時6分在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生5 5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緯33 58度,東經93 01度。震中5公里
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生5.5級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2024-03-07 20:42:04據中國地震臺網正式測定,3月7日18時6分在青海玉樹州雜多縣發生5 5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于北緯33 58度,東經93 01度。震中5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