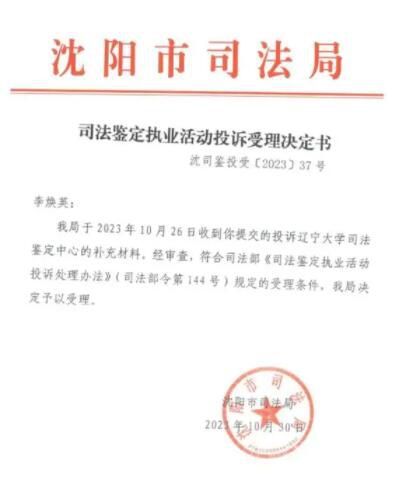法官告訴你怎樣保護孩子不被欺凌 校園欺凌行為如何界定?
導讀:近期發生的未成年人惡性案件,引起人們對校園欺凌的關注。近年來,隨著民法典、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規定的不斷普及,...

近期發生的未成年人惡性案件,引起人們對校園欺凌的關注。
近年來,隨著民法典、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規定的不斷普及,在家長、學校、未成年人保護機構等主體的共同努力下,“校園欺凌”現象得到有效治理,但此類事件并未被杜絕,因欺凌行為引發的民事和刑事案件仍時有發生。
這個游蕩在未成年人健康成長背后的“幽靈”究竟如何辨別?由此造成的傷害應該如何賠償?哪些主體對此該負責任呢?
提問1
校園欺凌行為如何界定?
某校學生王某、肖某懷疑同宿舍室友李某偷拿了自己的物品,她們搜查了李某的書包,但一無所獲。此舉雖未導致沖突,但使得李某與王某、肖某及其他室友關系不睦。事后,李某母親彭某找到學校反映情況,老師調查了事情經過并給李某調換了宿舍。一周以后,李某丟失了100元,她懷疑是王某偷竊,為此與王某和肖某發生爭執,王某、肖某認為李某故意誣陷她們偷錢,爭吵中互相推搡,后雙方被人勸開,此后幾人再未有任何交流。半年后,李某因疫情停課在家,父母發現她每天無故哭泣,李某稱同學在背后說她壞話,擔心同學害她。經醫院檢查,李某被診斷為精神分裂癥。后李某將王某、肖某訴至法院,要求判令二人共同賠償約16萬元。
法院審理后認為,現有證據無法證明王某、肖某的行為與李某患病存在因果關系,涉事學生間發生的矛盾沖突尚達不到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所定義的欺凌行為,矛盾沖突尚在一般正常人的心理承受范圍,不足以致嚴重精神損害,因此駁回了李某的訴訟請求。
法官解讀
根據未成年人保護法的相關規定,“校園欺凌”是指發生在學生之間,一方蓄意或者惡意通過肢體、語言及網絡等手段實施欺壓、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傷害、財產損失或者精神損害的行為。
實踐中,“校園欺凌”行為的構成一般有五個要素:一是主體,校園欺凌的雙方是學生,不包括老師或校外人員;二是主觀因素,欺凌者主觀上有蓄意或惡意心理,欺凌者明知自己的行為會給被欺凌者造成不利后果,而仍有意為之;三是地點,欺凌行為可能發生在校園內,也可能發生在校園外,或者發生在網絡虛擬空間;四是行為方式,包括毆打身體、恐嚇威脅、言語侮辱等一種行為或疊加的多種行為;五是損害后果,不論是身體傷害,還是財產損失、心理傷害,都屬于欺凌造成的損害后果。
校園生活中,同學之間的沖突在所難免。是否存在“校園欺凌”,應當根據沖突的程度、發生原因等綜合判斷。如沖突并非持續發生、程度嚴重,不存在蓄意或惡意攻擊情形,不宜認定雙方之間的沖突行為構成“校園欺凌”。
提問2
能否要求賠償精神損害?
張某與劉某、羅某、蔡某、畢某是同校同學。一日,張某與羅某因瑣事發生口角沖突,雙方相約超市門口見面。張某到達后,發現羅某攜劉某等候,劉某直接扇了張某幾耳光,并要求其向羅某道歉。張某道歉后,劉某等放其離開。幾天后,張某在籃球場打球,劉某與蔡某再次毆打了他。幾周后,張某在書店讀書時,劉某讓畢某帶其去KTV陪唱,在KTV中劉某強迫張某光著上身唱歌。后張某精神恍惚,被家人送往醫院,經檢查發現張某患上重度抑郁癥。張某起訴劉某、羅某、蔡某、畢某,要求賠償醫療費、健康咨詢費、護理費、精神損失費等。
法院審理后認為,根據各方陳述,能夠證實張某被欺凌的事實。各被告多次實施欺凌行為與原告張某所患抑郁病情存在因果關系,與張某抑郁發作的病情惡化直接相關,各被告應對張某的損失承擔連帶賠償責任,最終判令劉某、羅某、蔡某、畢某賠償張某醫療費等各項費用,其中包含精神損害撫慰金。
法官解讀
校園欺凌對被欺凌者造成的損害包括人身傷害、財產損害和精神傷害三種類型,而且經常存在交叉重疊的情形。對于人身傷害,欺凌者需要賠償醫療費、護理費等;對于財產損害,被欺凌者應當獲得經濟賠償。但對于欺凌造成的精神傷害,往往難以撫平,許多被欺凌者陷入自我否定和精神內耗之中,在此情形下,被欺凌者有權利主張精神損害賠償。具體裁判過程中,是否支持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主要考慮三個因素:一是被欺凌者人身權益遭到侵犯,單純的財產損害一般不會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二是被欺凌者產生嚴重精神損害的后果,對于“嚴重”的認定,需結合欺凌者的主觀狀態、欺凌方式、欺凌場合和被欺凌者的精神狀態等具體情節加以判斷;三是欺凌行為與精神損害后果有因果關系。
本案中,劉某、羅某、蔡某、畢某恃強凌弱,仗著人多勢眾,有扇耳光等人身傷害行為,也有強迫脫衣等侮辱行為,直接造成張某患上重度抑郁癥,因此劉某、羅某、蔡某、畢某應當賠償醫療費,也應當向張某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
提問3
學校盡責后還要賠付嗎?
王某與曲某、阿某、吳某就讀于同一中學。曲某、阿某、吳某曾分別多次毆打、敲詐王某。一日晚自習后,曲某與王某因口角發生糾紛,后王某去廁所過程中被曲某攔截毆打,學校得知后,隨即安排工作人員送王某到醫院治療,并通知其父。同時,學校對相關事件進行了調查,發現阿某先后多次向王某索要款項共計800元,阿某家長將800元歸還給了王某父親。王某申請長期病假在家,學校安排德育處教師和班主任多次上門看望他,并對其進行心理輔導。后王某前往醫院檢查,被認定患有抑郁癥。王某起訴曲某、阿某、吳某及某中學,請求賠償醫療費、護理費等9萬元。
案件審理過程中,法官調查發現,該校每學期都會邀請法治副校長開展兩次關于校園欺凌的專題講座,并設置了舉報箱。法院審理后認為,曲某、阿某、吳某通過毆打、索要錢款等欺凌行為,致王某精神抑郁,三者應當對自身行為給王某造成的傷害承擔賠償責任。在此過程中,學校盡到了保護義務,對欺凌行為的發生沒有過錯,并且針對校園欺凌等情形采用多種形式進行了廣泛深入宣傳,已履行了對學生安全教育、管理的職責,因此不應承擔賠付責任。經核算,最終法院判令曲某、阿某、吳某的法定代理人共同賠償王某約6萬元。
法官解讀
校園欺凌涉及的民事賠償責任承擔主體一般為欺凌者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是幼兒園、學校等教育機構。欺凌者應當對自己的欺凌行為負責。如欺凌者作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其父母要對其行為承擔替代的侵權責任。深究欺凌行為的背后,欺凌者的父母對子女欠缺關注和愛護,未履行作為父母的教育引導責任是造成子女成為施暴者的主要原因之一。對于學校來講,學校負有教育、管理職責,如果未盡職責導致未成年人被欺凌,學校也應承擔相應的責任。
本案中,學校在該欺凌行為發生前,已經通過開展講座、設置舉報信箱等積極措施避免校園欺凌現象的發生,事件發生后也能夠采取妥當措施處置相關行為,應當認定學校盡到了教育、管理職責,不應因此次欺凌事件承擔責任。
提問4
學校“視而不見”是否擔責?
某中學十余名在校生結成名為“青龍會”的小團體,張某是其中一員。張某懷疑同學孫某向老師舉報其私藏手機,課間將其約至衛生間進行威脅恐嚇。孫某否認,張某警告:“這幾天放學后路上小心點!”后張某聯系“青龍會”其他成員將孫某帶到學校小樹林輪流對其毆打,但未形成外傷。孫某將相關情況告知老師,老師對實施毆打的成員進行了口頭批評教育,認為這是同學之間的打鬧,未再進行處理。張某等人隨后以被老師批評為由將孫某帶至校外,再次對孫某進行毆打,并威脅“如果再報告老師,我們就打斷你的腿”。此次事件造成孫某多處軟組織挫傷,孫某將張某等人及學校訴至法院,要求判令各方承擔醫療費、精神損害撫慰金等。
法院審理后認為,根據張某等人在事件中的作用及學校的過錯程度,被告中學與其余被告應各承擔對孫某損失50%的賠償責任。本案是較為典型的校園欺凌事件,最先只是張某等人在校園內對孫某實施欺凌行為,學校對此并未及時發現并作出合理處置;其后欺凌行為發生雖在校園外,但也是第一次欺凌的延續,學校在肩負預防校園欺凌的責任中存在較大不足,應當對孫某的損失進行賠償。最終法院判令張某等人及學校共同賠償孫某5萬元。
法官解讀
在校園欺凌事件中,學校的角色是特殊的,既是發現危險的“吹哨者”,又是保護受欺凌學生的第一責任人,學校有義務也有條件展現更大的作為,守好反校園欺凌第一關。在校園欺凌事前預防措施上,學校需要防患于未然,建立周邊重點場所巡查制度,開展常態化防止學生欺凌摸查,對有欺凌苗頭的行為進行及時干預、控制。欺凌事件發生后,學校要立即組織校醫救治受欺凌者,成立學生欺凌治理委員會,對欺凌者作出處理決定,同時將該決定公之于眾,以便發揮教育和引導作用。在欺凌事件的事后處理上,學校需要安排心理咨詢師或專業人員展開對欺凌者和被欺凌者的心理輔導,組織雙方家長見面協調解決問題,化解彼此矛盾。
本案中,學校在事前未察覺到學生中“青龍會”小團體的存在,未采取有效措施防范校園欺凌行為的發生。發現欺凌事件后,未能對欺凌者給與恰當的處置,也未能對被欺凌者給與必要的關注和保護,未采取有效措施阻止后續欺凌事件的發生,學校應當對孫某的損失承擔賠償責任。
法官寄語
多方攜手根治校園欺凌
根治校園欺凌,我們該怎么做?
一是增加家庭關愛,矯正家庭錯位。孩子雖在校,家長也有責。父母應該和孩子保持良好的溝通,建立信任,培養孩子形成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讓未成年人擁有健全的人格。
二是法治教育+心理輔導,補齊學校失位。學校應該采取法治教育等多種措施加強對校園欺凌的防范和識別,積極開設心理課程,舉辦心理健康講座,幫助未成年人健康成長,一旦發現存在欺凌行為,果斷采取措施,將傷害后果降到最低。
三是多方攜手共同治理,彌補社會缺位。校園欺凌的防范和治理,僅僅依靠家長和學校是不夠的,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司法機關、教育行政部門、婦聯等主體以及我們每一個人,都應該貢獻各自的力量,這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我們每個人對民族未來應負的責任。
下一篇:最后一頁
-
 法官告訴你怎樣保護孩子不被欺凌 校園欺凌行為如何界定?2024-03-27 09:46:20近期發生的未成年人惡性案件,引起人們對校園欺凌的關注。近年來,隨著民法典、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規定的不斷普及,
法官告訴你怎樣保護孩子不被欺凌 校園欺凌行為如何界定?2024-03-27 09:46:20近期發生的未成年人惡性案件,引起人們對校園欺凌的關注。近年來,隨著民法典、未成年人保護法、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法律規定的不斷普及, -
 廣州婦兒中心身高普查系謠言 社會醫療機構冒用其名稱2024-03-27 09:43:252024年3月26日謠 言 廣州婦兒中心開展身高普查等公益普查項目?真相:近期,有社會醫療機構冒用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以下簡稱廣州婦兒
廣州婦兒中心身高普查系謠言 社會醫療機構冒用其名稱2024-03-27 09:43:252024年3月26日謠 言 廣州婦兒中心開展身高普查等公益普查項目?真相:近期,有社會醫療機構冒用廣州市婦女兒童醫療中心(以下簡稱廣州婦兒 -
 俄恐襲遇難者中120人身份已確認 暫未發現疑似中國人姓名2024-03-27 09:38:09當地時間3月26日晚,俄羅斯緊急情況部更新了一批莫斯科州音樂廳恐襲事件的遇難者名單,目前已有120名遇難者的身份得到了確認。3月22日晚,
俄恐襲遇難者中120人身份已確認 暫未發現疑似中國人姓名2024-03-27 09:38:09當地時間3月26日晚,俄羅斯緊急情況部更新了一批莫斯科州音樂廳恐襲事件的遇難者名單,目前已有120名遇難者的身份得到了確認。3月22日晚, -
 國足4-1大勝新加坡 武磊2球1助攻2024-03-27 09:39:13北京時間3月26日,2026世界杯預選賽亞洲區第二階段C組第4輪,中國隊4-1主場戰勝新加坡隊。26日,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36強賽中
國足4-1大勝新加坡 武磊2球1助攻2024-03-27 09:39:13北京時間3月26日,2026世界杯預選賽亞洲區第二階段C組第4輪,中國隊4-1主場戰勝新加坡隊。26日,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亞洲區預選賽36強賽中 -
 開封王婆五年前在角落練舞 沒有誰是隨隨便便成功的2024-03-27 09:36:34近日,河南開封王婆五年前在角落練舞的視頻曝出,舞臺雖小但王婆依舊認真對待角色。網友評論:沒有誰是隨隨便便成功的。前不久,河南開封萬
開封王婆五年前在角落練舞 沒有誰是隨隨便便成功的2024-03-27 09:36:34近日,河南開封王婆五年前在角落練舞的視頻曝出,舞臺雖小但王婆依舊認真對待角色。網友評論:沒有誰是隨隨便便成功的。前不久,河南開封萬 -
 小林制藥保健品已致2死106人住院 呼吁消費者停用受影響的產品2024-03-27 09:34:533月27日消息,據NHK報道,日本厚生勞動省26日公布了因攝取含有小林制藥公司紅曲成分的保健品后發生的第二例死亡案例,入院人數已增至106人
小林制藥保健品已致2死106人住院 呼吁消費者停用受影響的產品2024-03-27 09:34:533月27日消息,據NHK報道,日本厚生勞動省26日公布了因攝取含有小林制藥公司紅曲成分的保健品后發生的第二例死亡案例,入院人數已增至106人 -
 坐著高鐵“慢”賞花 成為今年春游賞花的新時尚2024-03-27 09:32:56春季是踏青賞景的大好時節,隨著高鐵新線的陸續開通運營,乘坐高鐵快旅慢游成為今年春游賞花的新時尚。去婺源看萬畝油菜花、去漢中打卡美人
坐著高鐵“慢”賞花 成為今年春游賞花的新時尚2024-03-27 09:32:56春季是踏青賞景的大好時節,隨著高鐵新線的陸續開通運營,乘坐高鐵快旅慢游成為今年春游賞花的新時尚。去婺源看萬畝油菜花、去漢中打卡美人 -
 推薦可能認識的人或是一種冒犯 不要給我推薦可能認識的人了2024-03-27 09:31:02近日,不要給我推薦可能認識的人了話題登上熱搜,引發不少網友吐槽。對此,媒體評:推薦可能認識的人或許是一種冒犯。據3月25日《南方都市
推薦可能認識的人或是一種冒犯 不要給我推薦可能認識的人了2024-03-27 09:31:02近日,不要給我推薦可能認識的人了話題登上熱搜,引發不少網友吐槽。對此,媒體評:推薦可能認識的人或許是一種冒犯。據3月25日《南方都市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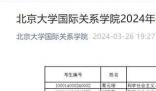 考生蔡元培北大復試仍是專業第一 網友:你們的校長回來啦2024-03-27 09:27:173月26日晚,據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公布的碩士復試成績信息顯示,此前備受關注的考生蔡元培復試成績仍是專業第一。3月26日晚,據北京大學國
考生蔡元培北大復試仍是專業第一 網友:你們的校長回來啦2024-03-27 09:27:173月26日晚,據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公布的碩士復試成績信息顯示,此前備受關注的考生蔡元培復試成績仍是專業第一。3月26日晚,據北京大學國 -
 內蒙古根河極光美景驚艷亮相 美景持續了整整4分鐘2024-03-26 13:29:1824日起,地磁活動逐漸活躍。受其影響,內蒙古根河市上空出現了罕見極光,美景持續了整整4分鐘。據中國氣象局消息3月24日、25日和26日三天將
內蒙古根河極光美景驚艷亮相 美景持續了整整4分鐘2024-03-26 13:29:1824日起,地磁活動逐漸活躍。受其影響,內蒙古根河市上空出現了罕見極光,美景持續了整整4分鐘。據中國氣象局消息3月24日、25日和26日三天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