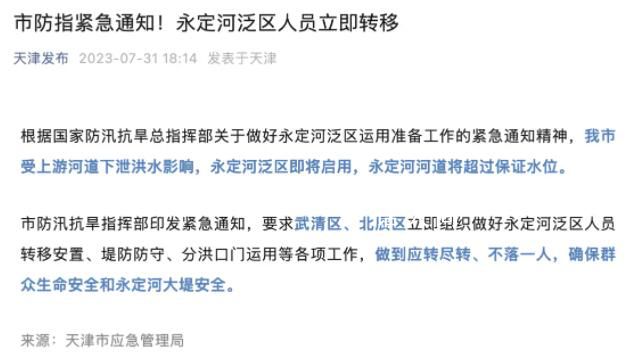農村出現嚴重空心化現象 農村只剩老人和兒童
導讀:2024年春節,記者在重慶農村鄉下發現,因青壯年大部分外出打工,農村只剩老人和兒童,導致農村出現嚴重的空心化現象。2024年春節,《中國經...
2024年春節,記者在重慶農村鄉下發現,因青壯年大部分外出打工,農村只剩老人和兒童,導致農村出現嚴重的“空心化”現象。

2024年春節,《中國經營報》記者在重慶農村鄉下發現,因青壯年基本上全部外出打工,農村只留下年齡超過70歲的老人和還在讀書的少年、兒童,“一老一少”的人力結構,導致農村出現嚴重的“空心化”現象,土地撂荒突出,收入缺乏支撐。
針對農村“空心化”,當地駐村干部和經濟學者給出了一些具體建議,但也同時表示,更需要有頂層設計。
重慶市目前正在推進學習浙江省“千萬工程”來解決相關問題,并推進鄉村振興。當地群眾對浙江“千萬工程”實踐中的“農業標準地”改革頗為期待。
“空心化”憂慮
“近些年,除了春節時年輕人回來幾天,其他時間村里基本上都只剩一些老年人和留守小孩了。”正月初四(2月13日)時,重慶市墊江縣某鎮某村村民組長程三說,年輕人在老家待不住,全都出去打工了。
出去打工的原因很簡單:該村民小組所在的區域,人均只有八分地(0.8畝),上次分地是幾十年前,所以現在30歲以下的村民,自己名下基本上沒有土地。按說,要等原來分到承包地的人去世后,騰出土地指標,后面沒土地的人才有望排隊分到土地。
“但最近二十幾年來,年輕人已經不再愿意種地了。”程三說。
土地賬很好算,即使人均有1畝地,不管是種水稻,還是種小麥、玉米、高粱,哪怕是換季輪種讓土地一直不閑著,年收入最多也只有1200—1400元,這還沒扣除人工費用和肥料錢,扣除這兩樣,實際年收入甚至只有三五百元。
“為什么不搞點養殖業?譬如養雞或者養鴨、養豬?”記者問。
“農村搞養殖業,現在基本上都是散養,扣除人工和飼料錢后,養得多虧得多,所以大家都不養了。”程三說,農村散養根本沒辦法跟城里的規模養殖業競爭,加上現在村里平時常住人口主要是“一老一少”,僅有的一點養殖業,也主要是村民自己養來吃的雞、鴨和豬,極個別有精力的村民會適當多養幾只,出欄后會出售貼補家用。
“還有沒有其他副業可做?”記者問。
“沒有了,現在村里‘一老一少’的人口結構,上是70歲以上,下是17歲以下,去掉80歲以上和12歲以下的人,剩下的也只能算是半個勞動力,現在連播種、收割,基本上都是在外面請人做,人力成本是每人每天給150元的工錢。”程三說。
自己干不了,請人干又太貴,所以村里的地有不少是荒著的,根本沒人種。
“我看到村里靠西的‘黃土坡’上前些年‘退耕還林’滿坡種的桉樹2023年也全部砍掉了,這是不是‘退林還耕’?那些地現在是誰在種?”記者問。
“上面安排來集中砍的,桉樹對水資源影響過大,桉樹砍掉后那些地也沒人去種,村里(生產大隊)就請人來種上了一些東西,也沒人去管理。”程三說,村民在山坡腳下自己的地都沒人去種,山坡上的“公家的地”,更沒有精力顧及。
“村里留守的人,有做農活經驗的現在都是7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基本上沒人能擔糞去爬近200米的坡上種地了,這個年紀,自己去把坡上的糧食收割回來,也很艱難,所以就不種了。”程三說,現在外出打工基本上是村里人的唯一出路:在大城市,月收入至少3000—5000元,雖然也辛苦,一年下來總歸有4萬—6萬元的總收入,這比窩在鄉下家里務農收入要高20倍,這個賬很容易算,所以年輕人全都走了,去沿海或城里打工去了。
這種情況是否具有普遍性?
重慶市某報業集團下放到某縣的駐村“第一書記”李巡稱,這不是個案,是普遍現象。目前農村的“空心化”問題很嚴重,土地撂荒問題也較為突出,表面上看,“18億畝耕地紅線”是守住了,但是土地沒人種的現象仍很刺眼。
“現在我們村的解決辦法是,請人種一些地,但這不是根本的解決辦法。”李巡稱,“大家都知道存在這個問題,但都沒有解決辦法。”
“即使把糧食價格翻2倍、3倍、5倍也沒人種,因為一是干農活是體力活,太辛苦、太累;二是城鄉收入差距達到了20倍;三是農村產出的糧食及養殖產品因過于零散,難以低成本快速賣到城里。”李巡說,何況糧食價格還不可能漲2—5倍。
次第城鎮化
“春節后我還會去深圳。”程三所在村民小組的村民吳成稱,他在深圳打工超過25年,前些年已經做到了一個生產廠廠長的位置上,之前主要因為疫情原因,回家休息了兩三年。疫情后,他再次赴深圳打工,原因在于一是已經不適應鄉下的生活及節奏了;二是返鄉后基本上沒有任何收入,長期坐吃山空,總不是辦法,所以不得不出去。
不過這一次吳成的妻子沒有跟隨他一起南下,她選擇了“返鄉創業”。
所謂創業,就是在縣城開店。然而,2023年,吳成妻子開的奶茶店垮了,另開了一個韓國料理店,后來也開不下去了,休整兩個月,又去開了一個“麻辣串串”店,也基本沒什么生意。一年多下來,夫妻二人打工20多年積累的幾十萬元積蓄,基本都被“創業”消耗了。
吳成妻子的經歷,也許只是個案。
據重慶市人社局2023年11月3日公布的信息,2022年,該市全年促進農民工返鄉入鄉創業就業17.32萬人,其中,返鄉創業2.72萬人。創建農民工返鄉創業園69個,全年實現總產值371.8億元,吸納就業5.78萬人。
2023年,重慶市“返鄉創業”人員巨幅飆升。
據重慶市人社局2024年1月26日發布的消息,截至2024年1月26日,該市農民工已返鄉87萬人,其中市外返鄉73.2萬人,占市外務工農民工總數的28.3%;市內返鄉13.8萬人,占市內鄉鎮外務工農民工總數的3.6%。
該市從市外返鄉人員中,從廣東、浙江、福建返鄉的最多。
2022年,重慶市外出務工人員約為791萬人。所以當沿海用工情況發生變化時,返鄉的人數便不會太少。
程三所在的村民小組,之所以留守的人群基本上只剩“一老一少”,另一個原因還在于,村里經濟條件稍微好一點的家庭,要么在縣城買房搬走了,要么在附近鎮上買房搬走了。
幾年前,該村民小組的東側修建了一條一級公路,往來車輛時速可達70公里。加上此前修建的村村通公路,該村比其他山區或偏遠區縣有很好的交通便利優勢。不過盡管如此,鄉下的基礎設施及配套設施,以及商業化便利程度,還是趕不上鄉鎮、縣城,因此大家都搬到了縣城、鄉鎮。
不知道這種“城鎮化”,是否體現在相關統計中。
重慶市發改委向媒體披露的信息顯示:“2022年,重慶常住人口城鎮化率70.96%,較2012年提高14.3個百分點;戶籍人口城鎮化率50.1%,較2012年提高10.7個百分點,新型城鎮化蘊藏的發展動能得到加快釋放。”
當地村民稱,其實這些搬到縣城、鄉鎮去住的人,絕大部分也只是把房子買在了這些地方,人還是照樣跑到沿海城市或附近大城市去打工,家里留下的依舊是“一老一少”,只是在縣城、鄉鎮住的人,已經初步完成了城市化進程,他們的收入不再依賴土地,不需要再種地。
不過也有一些人,選擇在老家修建房屋。這類人分成三種:第一類是在縣城、鄉鎮購買了商品房,但仍在老家重慶修建房屋的人,這類房屋基本上全年空置,僅春節時有人回來住幾天;第二類是常年在外打工的人群,賺錢后回家修房,以求年老返鄉,有一個“落腳處”;第三類是村里的“首富”,將老家的房屋修成了別墅。
程三所在村民小組的鄰村幾個兄弟,據說前些年做房地產掙錢過億元,在老家修建了豪華程度不亞于大城市別墅的幾幢樓,這些樓外墻上還采用了全大理石干掛裝飾,是附近村“最靚的仔”。
不過,這些鄉村別墅跟其他農村房屋一樣,絕大多數時間都空著,無人居住。
如何破困局?
“以前春節打工回來會到農村聚會,現在基本在鄉鎮或者縣城都有房子,打工回來就把老年人接到鄉鎮或者縣城過年,這種現象越來越多。隨著年輕人對鄉愁越來越淡,怎么能苛求他們回去?”前述駐村第一書記李巡2月18日說。
這樣一來,不只是平日里“空心化”,逢年過節本該聚集人氣的時候,還出現了新的“空人化”現象,農村年味越來越淡。
“我寫了一些日記,有一些想法,但是還沒有完全系統思考這個問題。‘空心化’是不可避免的,要減少‘空心化’,其實就是解決人的問題。人怎么留下來?這是個系統問題。”李巡說,“農村人的發展、他們的未來、他們的后代怎么發展等問題,其實很復雜。”
他追問道:“如何讓農村產生吸引力?喊口號是不行的。所以,如何緩解農村‘空心化’問題,經濟專家也許比我更懂,因為這是一個社會學問題,更是一個經濟學問題。”
重慶市前沿區域經濟研究院院長李勇2月19日稱,目前中國的農村“空心化”問題,表面上看是“無解”的,但實際上可以通過一些點上的突破,來逐步推進面上問題得到緩解或解決。
他建議的六大解決途徑分別是:一是進一步促成機關事業單位加大對口扶貧力度,并將縣、鄉機關干部及事業單位富余人員下沉到鄉村去,挖掘“一村一品”,通過他們來帶動鄉村振興。二是推動能人帶動,讓更多的能人當村支書,因為他們了解當地的情況,也在外面開過眼界,還有資本、有能力,讓他們來幫扶、帶動農村致富。三是產業帶動。四是靠發展特色旅游來帶動鄉村致富,特別是越偏僻、越荒涼的地方,獨特的風景會吸引游客,就會帶動經濟發展。五是搞一些鄉鎮整合,有些自然村和鄉鎮人丁稀少了,就要進行合并、整合,把人員集中起來,把土地集約利用起來,委托第三方進行綜合診斷并做方案,整體規劃,發展新農村。六是吸引主體在鄉、村的示范性養老,吸引離退休人員返鄉養老,人來了,錢就跟著來了。
李勇說,他所在的機構近年來為川渝多個地方做過相應方案,且多次前往浙江多地調研,目前農村發展的根本性制度問題,還在于農村用地的土地改革政策,還需要先行先試,要敢于試點,不然外來資本沒法落地。譬如他目前正在做的成都青城山后山半山腰的一個方案,計劃推進農村集體用地入市,騰出200—300畝農村建設用地來盤活整個項目,但是,暫時卡在用地政策無法突破上。
李勇說,農村要吸引資本,農村建設用地必須要突破,如果沒有土地證,權益就得不到保護,資本和人員就不會來,因為投資權益得不到保障。原國土資源部此前已經有一個農村集體土地入市的規定,但是“現在已經沒有人來推這個事情”。
重慶市一位不愿具名的經濟學者稱,據他此前對浙江省“千萬工程”的實地調查、了解,其實質是通過創新體制,引入各界資本下鄉,全面盤活農村土地資源。
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縣魯家村就有著成功經驗。“公司+村+家庭農場”模式,吸引投資20億元,一個浙江北部的貧困村,一舉成為國家級標桿項目——在這一操作模式中,核心是浙江在用地政策上,推出了“農業標準地”這一政策創新。
在“農業標準地”這一政策框架下,以前嚴禁建房的耕地中的3%—7%的土地,可以合法建房、建廠。
2024年1月5日,重慶市召開“市委農村工作會議暨重慶市學習運用‘千萬工程’經驗加快建設巴渝和美鄉村現場推進會”,重慶市委書記袁家軍在會上提出,要“深入實施‘四千行動’,打好鄉村全面振興主動仗”。
“千萬工程”是**在浙江時推進的“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是浙江“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在基層農村的成功實踐。
“四千行動”,是指千萬畝高標準農田改造提升行動、千億級生態特色產業培育行動、千萬農民增收致富促進行動、千個巴渝和美鄉村示范創建行動。
截至記者發稿,群眾最為期待的“農業標準地”是否會在重慶迎來創新和突破,尚未有最新消息。
上一篇:中國航天再添國之重器 構建三位一體天地一體化研究體系
下一篇:最后一頁
-
 農村出現嚴重空心化現象 農村只剩老人和兒童2024-02-28 17:54:042024年春節,記者在重慶農村鄉下發現,因青壯年大部分外出打工,農村只剩老人和兒童,導致農村出現嚴重的空心化現象。2024年春節,《中國經
農村出現嚴重空心化現象 農村只剩老人和兒童2024-02-28 17:54:042024年春節,記者在重慶農村鄉下發現,因青壯年大部分外出打工,農村只剩老人和兒童,導致農村出現嚴重的空心化現象。2024年春節,《中國經 -
 中國航天再添國之重器 構建三位一體天地一體化研究體系2024-02-28 17:46:532月27日,由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聯合建設的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在哈爾濱通過驗收。這是我國航天領域首個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
中國航天再添國之重器 構建三位一體天地一體化研究體系2024-02-28 17:46:532月27日,由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航天科技集團聯合建設的空間環境地面模擬裝置在哈爾濱通過驗收。這是我國航天領域首個國家重大科技基礎設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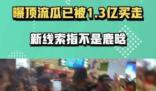 男演員大瓜被1.3億買走 狗仔張小寒成為了公眾指責的對象2024-02-28 17:37:07娛樂圈近日傳出一則令人矚目的消息,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某頂級流量明星的隱私信息被以1 3億元的價格交易。這一交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男演員大瓜被1.3億買走 狗仔張小寒成為了公眾指責的對象2024-02-28 17:37:07娛樂圈近日傳出一則令人矚目的消息,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某頂級流量明星的隱私信息被以1 3億元的價格交易。這一交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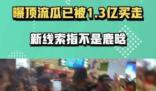 男明星1.3億買走塌方信息 曝頂流瓜已被1.3億買走U BB2024-02-28 17:36:29娛樂圈近日傳出一則令人矚目的消息,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某頂級流量明星的隱私信息被以1 3億元的價格交易。這一交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男明星1.3億買走塌方信息 曝頂流瓜已被1.3億買走U BB2024-02-28 17:36:29娛樂圈近日傳出一則令人矚目的消息,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某頂級流量明星的隱私信息被以1 3億元的價格交易。這一交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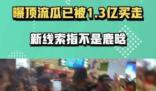 1.3億買的是誰的瓜 曝頂流瓜已被1.3億買走662024-02-28 17:34:18娛樂圈近日傳出一則令人矚目的消息,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某頂級流量明星的隱私信息被以1 3億元的價格交易。這一交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1.3億買的是誰的瓜 曝頂流瓜已被1.3億買走662024-02-28 17:34:18娛樂圈近日傳出一則令人矚目的消息,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某頂級流量明星的隱私信息被以1 3億元的價格交易。這一交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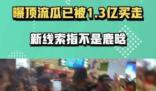 知情人曝頂流瓜已被1.3億買走,給出四個關鍵條件2024-02-28 17:34:51娛樂圈近日傳出一則令人矚目的消息,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某頂級流量明星的隱私信息被以1 3億元的價格交易。這一交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知情人曝頂流瓜已被1.3億買走,給出四個關鍵條件2024-02-28 17:34:51娛樂圈近日傳出一則令人矚目的消息,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某頂級流量明星的隱私信息被以1 3億元的價格交易。這一交易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
 董宇輝回應不理解女生做美甲 對老師著裝打扮有要求2024-02-28 16:30:39鞭牛士2月21日消息,話題 董宇輝解釋為何不讓做美甲 今日登上抖音熱搜。董宇輝日前在直播時對此前的「不能理解美甲」的言論進行回應。董宇
董宇輝回應不理解女生做美甲 對老師著裝打扮有要求2024-02-28 16:30:39鞭牛士2月21日消息,話題 董宇輝解釋為何不讓做美甲 今日登上抖音熱搜。董宇輝日前在直播時對此前的「不能理解美甲」的言論進行回應。董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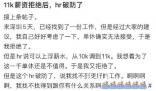 當我拒絕11k薪資后HR破防了 雙休和單休區別大嗎2024-02-28 16:29:29有網友發帖稱:因為接受不了單休,剛畢業半年的我拒絕了11k的薪資,沒想到HR卻破防了……隨后,話題詞 當我拒絕11K薪資后HR破防了 沖上熱搜
當我拒絕11k薪資后HR破防了 雙休和單休區別大嗎2024-02-28 16:29:29有網友發帖稱:因為接受不了單休,剛畢業半年的我拒絕了11k的薪資,沒想到HR卻破防了……隨后,話題詞 當我拒絕11K薪資后HR破防了 沖上熱搜 -
 上海一飯堂發生情殺案致2人死亡 警方已經介入調查2024-02-28 16:26:182月26日上午,上海市徐匯區田林東路的宜德飯堂(田林店)內發生了一起令人震驚的兇殺案。據初步了解,案件導致兩人當場死亡,兇手自殺未遂,
上海一飯堂發生情殺案致2人死亡 警方已經介入調查2024-02-28 16:26:182月26日上午,上海市徐匯區田林東路的宜德飯堂(田林店)內發生了一起令人震驚的兇殺案。據初步了解,案件導致兩人當場死亡,兇手自殺未遂,